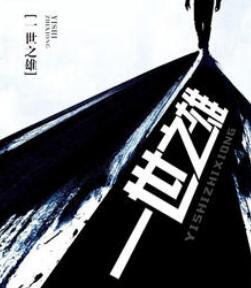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绝色毒妃权谋天下免费阅读 > 第466章 梅易死了(第2页)
第466章 梅易死了(第2页)
月明星稀,夜风冰寒,有马蹄声渐渐逼近冰原一带。
为首的男子披着斗篷,大半张脸都被帽沿阴影笼罩,看不清晰,唯有瘦削的下巴被月光照得莹和。
“停下!什么人?”放哨的士兵发现,连忙上前拦截。
一块令牌被丢入士兵的怀中,士兵低头一看,膝盖差点软了,哪里还敢拦?
“王妃娘娘!王妃娘娘!”帐外有人喊着苏鱼。
苏鱼正坐在案桌前,闻声抬头,帐帘被掀开,如松柏高大直挺的男人大步进来,带入一阵寒凉的风。
他将身上的斗篷解下,大步走向苏鱼。
苏鱼既惊又喜,连忙扔下毛笔站起身,迎了上去,“长风,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景长风张开双臂,将她拢进怀里,力道大得似是想将她揉进骨血里,下颚抵在她的肩上,疲累的双眼微阖。
他想极了她,不知不觉,他们分开已经小半年了。
直到将金钦幽完全拖住,他就马不停蹄的赶来,迫不及待地想见她。
“景长风,你怎么不说话呀?”两条铁臂让她觉得被勒得慌,苏鱼忍不住推了推他。
“娘子,我好累啊,我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过觉了。”
景长风的凛冽铁血消失不见,他说话软绵绵的,像极了撒娇的小猫咪。
苏鱼的心,霎那间软了下来,反抱住他的背,“好好好,我再让你抱一小会,你就得乖乖去洗漱一番上床睡觉。”
景长风低低地应了一声,性感的喉音带着春风般的迷醉。
过了一会,景长风终于松开了她,外面有人抬进热水,景长风开始脱风尘仆仆的外衣。
苏鱼:“你先在这里洗,洗好了叫我,我先出去。”
谁知,景长风反手拉住她,“娘子,我刚刚衣裳是脏的,抱着你这么久,你身上肯定也脏了,不如来一块洗。”
说着,不容拒绝地将苏鱼拉过来。
欸?
她衣裳没脏啊!
*
帐内的油灯,燃至油尽也无人续。
第二日清晨,夙玉小跑过来,瞅见白砂就问:“白砂姑娘,我听说景长风来了,他人呢?”
正好,范从容也过来了,他也问道:“白砂姑娘,我有点事,想找一下王妃娘娘,不知她现在何处?”
白砂抬头看了看正至头顶的午阳,脸颊一红,心底盘算着怎么回答这二人。
她该怎么说?说主子跟殿下至今还没起床吗?
正在白砂为难之际,景长风从军帐内走出,他将门帘挂到一旁,倚在门框边上不羁地问:“找本王的王妃做什么?这儿是战场,可没有生意可做,范家主既送完了军饷,随行的户部侍郎早早回了京都,怎的范家主还留在这儿?”
他说话吊儿郎当,看向范从容是毫不掩饰的敌意,十分的幼稚。
哪怕知道范从容跟他的娘子绝无可能,但景长风每每瞧见范从容就觉得讨厌。
尤其是这种时候,范从容一看就想趁他不在偷偷跟他的女人献殷勤。
范从容不急不缓地笑道:“宸王殿下还不知道,草民已经投身军伍,成了王妃娘娘座下的一员小兵,现在自是有要事向王妃娘娘禀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