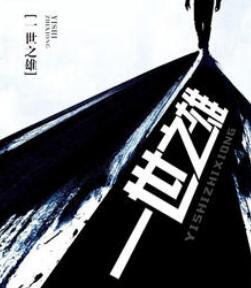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乱世情缘42 > 第五十五章 母爱的力量(第1页)
第五十五章 母爱的力量(第1页)
马灯一直亮着,女人灵巧麻利的身影,欢快地晃动在昏黄的光线下。
说实话,她的岁数并不大。
也许是显老的装束,和被困苦岁月磨砺得,使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一阵扑鼻的肉香,将祥子从心猿意马的遐想中,拉了回来。
痴呆燃烧的马灯,已被弥漫到了,带着浓重香味的蒸汽里。
屋内,显得更加昏暗迷离。
“大晚上的,咋还熬肉哩。”是里屋传来的声音。
祥子忙起身过去,女子也随后拎着马灯进了门。
欣喜地说:“你头先烧得直说胡话哩,腿上的口子溃了脓。
是这个过路的兄弟,给你治的伤,还上咧药。”
炕上的男人,忙坐起身,说:“多亏你哩,也不知让我说啥好哩。”
祥子忙摆手说:“不算啥,是我遇上咧。”
女人,胡乱地摆弄了一阵炕上的衣物,拧身麻利地将小桌支到炕上。
又将马灯,挂在屋顶吊下的木钩。
顿时,小桌便被笼罩在一片光明下。
女人,脸上表情活泛地说:“我闷了干肉锅贴,说话就好。
我到二爸家寻瓶酒去,你陪兄弟喝几盅。”
祥子刚要拦挡,女人的脚步,已经响在了屋外。
祥子疑惑地瞅了眼男人,试探的问道:“咋就让狼给扯咧?”
那人,丧气地长叹一声,说:“他妈地真倒霉,那天去打猎,见石崖子上卧着一只狼。
寻思着弄条狼皮褥子,就朝狼开枪咧。
哪知,枪上还冒着烟哩,就从石崖上窜出三条狼。
我来不及装枪药,看茬口不对,撒腿就跑。
才转身,一头狼就扑上来给咧一口,身子没站稳,就滚下咧崖。
亏得命大,落在咧老榆树顶上。不然,非跌死不可。”
祥子温和一笑,说:“听说狼都是合群的,轻易不单独出来。”
男人懊悔地一拍大腿,说:“嗨!是我大意咧。
打咧几年猎,还没吃过这号子亏哩。”
祥子冲他宽慰地说:“你的伤无大碍,我再给你留点药。
如果结了痂,就不用管。要是发痒出水,就先用酒洗一洗,再撒上药。
有个十天半月的,就能干活咧。”
男子冲他憨厚一笑,说:“多亏咧你,就多住些日子吧?”
祥子温和一笑,说:“我急着赶路,还有一百多公里路哩。”
男人有些吃惊地伸了伸舌头,小声说:“妈呀,走那么远。”
脚步响处,女人拎着两瓶酒,身后跟着被称作二爸的中年男子。
寒暄落座后,一盘焖肉和一盘玉米锅贴,便热气腾腾的端了上来。
原来,女人说的干肉闷锅贴。是把风干肉,和葱姜蒜调料闷在大锅里,再沿锅边贴上玉米饼。肉软了饼也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