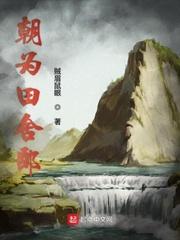456小说网>白虹贯日的贯是什么意思 > 第97章(第1页)
第97章(第1页)
>
卢棂反应过来,回首一看,还真在不觉中走出了巷子。
“既如此,臣告退了,殿下慢行。”
秦姝弯了眉梢,“好。”
卢棂驻在原地,目送她的离去,不由得有些出神,这位殿下若是能将心事放一放,总能笑得这般好看,该多好。
又摇了摇头,泼天的事儿压在肩上,恐怕换作是谁,都没法子轻松吧。
自嘲一笑,笑自己的天真。
-
其实能见着秦姝展颜的,还有那位。
秦姝对于他的敬重与信赖,是不亚于先帝的。
少时受罚得狠了,肯为秦姝这非亲非故的小女娃娃而向他进言之人,也只有这位老人家。
秦姝抿着唇,像模像样地走进祁府的书房,前脚刚跨进去,后脚还不等跟上来,脚下就被丢过来一本文书。
她默不作声地蹲下来拾起,并不翻开,只轻着步子继续往里探。
“你跟个猫儿似的做什么?当老夫耳力衰弱,人已经老了?”
女子立即顿足,恭敬地向屋子深处施礼。天色渐暗,里面又未点烛,她只依稀见着个人影负手而立,“小姝来给祁伯伯请安,怕惊扰伯伯休憩,故而没有叫人通报。”
“胡说八道。”里面那人一摆大袖,“你瞧瞧宫里都成什么样子了,谁还睡得着?”
听秦姝这边没了动静,祁牧之心里一惊,生怕她当了真,急急走出内室,果然见着女子手中捧着那本文书,孤独又凄清地垂首立于门口。
祁公年纪大了,深知这是个可怜孩子,暗骂自己说话没个分寸。上前来取回那本上奏指责陛下怠懒政事的文书,仔细敛去上面的灰尘,才抬首道,“老夫知道,这不怪你。”
阿姝的双睫颤了颤,“规劝君主,也是九层台的责任,是该怪我的。”
祁公将她扶起来,“什么事儿都揽在自己身上,对你有什么好处?要学得聪明些,别像谢家那小子似的,一根筋。”
阿姝破涕为笑,她还能学着了他?
祁公终于见着她露出笑模样,也知道她在笑什么,“说来也怪,谢家小子多年离京也就罢了,在外面野惯了,心眼少。你都在京里多久了,老夫上次瞧你,你与他还没这么相像。”
“可这几日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越发让我觉着,你与他的行事像极了。”
阿姝心里暗暗惊讶,只堪堪笑着,“那也是他像我。若不是我,他还不知道在哪躺着呢,我还拿这事诓他留在我身边学习来着。”
祁牧之引着她落座,端详着她,“你让他多跟你学着保命,也好。”
他似乎还有半句话,在嘴边斟酌了许久。
久得秦姝都忍不住放下茶盏看过来,他才换了种方式说出口,“你跟他学,虽说会了无遗憾,但极容易置于危墙之下。小姝,老夫是希望你们俩都能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