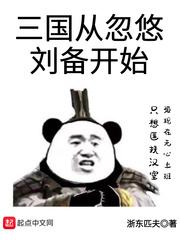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壶百年酒价格 > 第十七章 全被他杀了(第2页)
第十七章 全被他杀了(第2页)
留下白堕一个人在沟底,目瞪口呆。
“你早就能出去,还生什么火啊!”白堕气得扬起头来嚷嚷。
“你冷,而且我要想事情。”温慎从上面甩下根藤蔓来。
白堕拽住,试了好几次,最终在力竭之前,爬了出来。
待两人回到酒坊,已经是满天星辉了。
白堕到了住处,铃铛哭得眼睛都肿了,见到他立马扑上来:“您没死啊?”
“死了也没见你出去找找我。”白堕看他哭得好玩,故意逗他。
“我不去,”铃铛哑着嗓子,“大小姐带人出去找了,我就跟这等着,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就捅了老夫人,让她给您偿命!”
白堕哈哈大笑:“嗬,没看出来啊,这么讲义气?”
“您还笑?!”铃铛登时哭得更凶了。
白堕忙哄了半天,又把发生的事情讲了讲,铃铛才缓过气来,“您也是,自己一个伙计,掺和东家的家事做什么。”
说完,他伸手碰了碰白堕额头上的伤,又心疼起来:“等下次进粮,我非放两只老鼠进去,狠吃他一顿,叫那个老太婆随便打人!”
白堕笑着任由他胡说,自己洗了个澡,伤口也不处理,便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上工,所有人都默契地没有提白堕要被赶出泰永德的事。
赤水那头有伙计送了大曲过来,为了抢时间,大家伙儿都被拉去碎曲。
日头刚起来,温度正好。二子带人麻利地把酒坊大门前的空地清出来,黄灿灿地曲饼铺了一地。
伙计们拿着镐棍砸得大刀阔斧,白堕就比较憋屈了。他分到了细磨的活,和铃铛一起坐在几个姑娘中间,拿着小杵一点点把碎了曲块研成粉。
黔阳的姑娘性子爽朗,边干活,边唱起了甜甜的情歌来。不远处的汉子们看得赏心悦目,干活的膀子抡得更开了。
一行人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传来了一阵滴滴声。
很快,汽车在大门外停下,温慎和一个看起来有些瘦弱的青年人一起下了车。
那青年先开了口:“东西倒好,就是不知道价格上能否再商量一下。我也是背着父亲买这汽车的,一时拿不出那么多来。”
温慎还没说话,沈知行就风风火火地冲了出来,边路边喊:“东家!东家!”到了地方,他才终于注意到了周围好奇的眼神,偏头对着温慎耳语了起来。
温慎听完,脸色一紧,他像是想要躲什么人一样,带着青年往车上去,“访南兄,我们换个地方谈。”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老夫人由人搀着,一路从干活的伙计们中间穿过去,平日里的沉稳雍容,和她脚下的曲饼一样,早就不知道被踢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惕儿对我的孝心,”她带着一众老妈子挡在汽车前面,“哪个敢卖!”
温慎看起来非常为难,他先把同来的青年人妥当安置在一旁,才到近前去劝老夫人:“母亲,黔阳不比赤水,饷钱的事开不得玩笑。这汽车先卖了,等半个月后,尾款收上来,我再重新帮您买一辆。”
老夫人瞪圆了眼睛,气得两腮发颤,“你是不是样样都想压你弟弟一头?当家让你做了,酒坊让你管着,如今连买个汽车这样的小事,你都要抢他的功不成?”
说着,她向后推了温慎一把,“你犯不着在我面前表现,谁有孝心,我自己心里清楚!”
她的声音极大,半点都没想遮掩。周遭干活的人明面上忙着手里的活计,实则耳朵恨不得贴到他们那边去。
“我从没有这么样想过。”温慎尽力想压下老夫人的火气,“母亲,黔阳王行事狠辣,我听说就因为小农卖菜,泥水溅到了他手上,他就让人把整个村子都给烧了。三岁的娃娃哭闹扰了他的清净,他竟持刀把那孩子的皮给扒了!这样的人是说不清楚道理的……”
老夫人:“你少拿这些借口搪塞我,他一个土匪出身,无非是要钱而已,实在不行,还有你爹的那箱金子在,我就不信他敢把我们怎么样。”
温慎的眼神不自觉地闪了一下,良久,他无声地叹了一口气,“请母亲先回后院吧,这汽车我不动便是了。”
老夫人的表情这才稍稍松下来些,又寒着脸嘱咐几句,才带着人,慢慢回去了。
待她走远,温慎回身,带着几分愁色给买家赔不是:“对不住了,访南兄。家母的意思你也听到了,害你白跑一趟,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倒是可惜了。”那青年并没有为难他,只是语气里不无遗憾,他的眼神在汽车上驻足片刻,才摇头:“我自己回去就行,不麻烦了。”
“正好我进城里还有事,同走吧。”温慎坚定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青年没再推辞,同温慎一起上了车。
两人刚一离开,伙计们就炸开了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