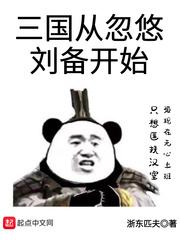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春雪润丰年 > 三十二(第1页)
三十二(第1页)
四个人环绕后山转了一圈儿,跑遍院子里的各个角落,坐在海风拂拂的客厅里休息,打开从横滨运来的用井水拔过的柠檬汁畅饮。于是,疲劳立即消除,个个心情振奋,打算赶在日落之前,到海里游上一游,接着分头准备起来。清显和本多系着学习院式的红色三角裤,穿着露着脊背和两胁缝着锯齿形针脚的棉布游泳衣,戴上草帽,等着动作缓慢的王子们。不久,王子们来了,他们穿着英国制的横纹海水游泳衣,肩头光裸着茶褐色的肌肉。
本多虽说是交往已久的老友,但夏天里清显未曾邀他到这座别墅来过。只在一个秋天,本多应约来这里拾过栗子。因此,本多和清显打从童年时代在片濑学习院游泳场共同游过一次海之后,再也未能在一起游过。况且那时候,两人还不像现在这样格外亲密。
四个人径直跑出庭园,穿过院外一带幼小的松林和毗连的田野,来到海滩之上。
下水前,清显和本多老老实实做体操,两位王子看到简直笑翻了。这笑声可以说是对他们一次轻微的报复,因为他俩只是远远眺望大佛而不肯跪拜。在王子们眼里,如此现代化的只为自己着想的这种戒律,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很可笑。
然而,正是这种狂笑表现了王子们罕见的轻松愉快的心情,清显很久没有看见过两位异邦的朋友如此欢乐的样子了。水中一阵畅游之后,清显早已忘记东道主照顾客人的义务,四个人分做两组,躺在海滩上,离得远远的,王子们用本国语交谈,清显他们用日语交谈。
落日包裹在薄云里,失去了先前酷热的势头,对于清显白嫩的肌肤尤为适合。他那只穿一件三角裤的湿漉漉的身子,痛痛快快仰面躺倒在沙滩上,紧闭着眼睛。
本多盘腿趺坐在他左侧的沙滩上,呆呆望着海水。海面十分平静,但波浪的景色使他感到很着迷。
他的视线的高度和海面的高度几乎相同,但奇怪的是,他突然觉得,眼前的大海到了尽头,陆地由此开始了。
本多一只手捧着沙子,倒腾到另一只手里,沙子漏光了,只剩下空空的掌心,他再次抓起一把沙子,但眼睛和心思全然被大海吸引住了。
海就在这里完结了。如此广阔的大海,如此充满活力的大海,就在眼前完结了!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没有比伫立于境界线上更加感到神秘的了。置身于大海和陆地如此壮大的分界线上,宛若站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一瞬之间见证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移转,此时的心境难道不是如此吗?本多和清显生活着的现代,也不外乎相当于一次潮涨潮退时的境界罢了。
……大海就在眼前完结了。
遥望远洋的波涛,就会明白,它们是经过多么漫长的努力,最后才不得不在这里宣告完结。于是,全世界所有海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企图,终于徒劳地结束了。
……然而,尽管如此,这是何等平稳而又亲切的挫折啊!波浪最后一圈儿微细的余波,立时失去纷乱的感情,同潮湿沙滩平滑的镜面化为一体,变成淡淡的泡沫,此时,身子重新退回了海里。
远洋里涌来的四段或五段的细碎的雪浪,各自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昂扬,或高腾,或崩溃,或融合,或退却……
那种显现出橄榄色柔软腹部的飞扬的水波,是扰乱的,怒号的,渐渐强化的怒号,变成一般的呐喊,而呐喊终将变成窃窃私语。巨大的白色的奔马,将变成小小的奔马,不久,横冲直闯的马队的马身消散了,最后,岸渚上只留下不住踢踏的雪蹄儿。
两道粗大的余波由左右张开着扇形,互相侵扰着渐次融入沙滩的镜面,其间,镜中的影像活泼地晃动起来,激荡的浪花奔涌着,映出锐利的纵长的形状,仿佛是闪光的霜柱。
退去的远方的波涛,同一道道奔涌而来的波浪相重叠,没有一道波浪背对着海岸,而是混成一体,一同咬紧牙关指向这里。可是向洋面望去,刚才岸渚上看似强劲的波浪,实际上呈现出稀薄而衰退的气象扩散开去。渐渐地,渐渐地流向远洋,海水变浓了,岸边海水稀薄的成分渐渐地被浓缩,被压挤,以致使水平线变成深绿色,无边的浓缩的青碧就会结成坚硬的晶体。虽然装点着距离和间隔,但惟有这种结晶才是海的本质。这种稀薄、慌乱的波的重复,最后凝结成的蓝色的晶体,那才叫大海呢……
想到这里,本多的眼睛和脑子都疲劳了。他转眼看看清显,从刚才起他就以为清显睡着了。
他那白皙而柔美的体躯,只裹着一条红色三角裤,形成鲜明的对比,微微起伏的雪白的腹部和三角裤上缘相接之处,闪耀着干沙和贝壳细末的光亮。清显偶而抬起左腕枕在头底下,本多发现他的左肋外侧,离开樱花蓓蕾般的乳头不远、平时被上臂遮盖的地方,集中生长着三颗小黑痣。
肉体的征象是奇妙的,虽然长期交往,但第一次发现朋友于不经意之间暴露出的身上的秘密,他不愿直盯着那些黑痣。本多闭上眼睛,眼皮内散放着强烈白光的夕空,鸟影一般鲜明地浮泛着三颗黑痣。不一会儿,那些羽翼临近了,显现出三只飞鸟的形状,向头顶上迫击而来。
本多又睁开眼,看到清显鼓动着秀美的鼻翼一呼一吸,微微张开的嘴唇之间,闪现着莹润而洁白的牙齿。本多的眼睛再次移向他胁肋上的黑痣,这回,他看到那些黑痣像沙粒一般深深嵌入清显白嫩的肌体。
如今,就在本多眼前,干燥的沙滩终结了,接近水线的沙地,随处分布着斑驳的白色沙堆,逐渐经水侵而变得黝黑起来;然而,那里却刻印着轻浅的波浪的浮雕,似化石一般密密麻麻镶嵌着小石子、贝壳和枯叶等物。而且,不论多么小的石子,都保留着退潮时的水痕,向着大海呈扇形张开。
不光小石子、贝壳和枯叶,海水冲上来的马尾藻、碎木片、稻秆和橘皮都一律嵌入其中了。既然如此,清显坚实而白嫩的肋部肌肉,嵌入极其微细的黑色的沙粒,也是很可能的。
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啊,本多思忖着,如何在不把清显弄醒的情况下,想办法帮他除掉。瞧着瞧着,那些微小的沙粒随着胸部的起伏而强健地运动着,不管怎么看,它们都不是无机物,而是清显肉体的一部分,本来那就是黑痣。
他总觉得,那黑痣背叛了清显肌体的优雅。
也许肌体感觉到被强烈的凝视,清显突然睁开眼,目光交汇,看到朋友一时惶惑起来,于是抬起颈项问道:
“能帮助我一下吗?”
“好的。”
“我来镰仓,名义上是陪王子们游玩,实际上是想给人一个我不在东京的印象,造成一种舆论,你懂吗?”
“我大致也猜到你的意图啦。”
“我会时常抛下你和王子们,悄悄回东京去。三天不见她,我就受不住啦。我不在时,你撒个谎瞒过王子们,万一东京家里来电话,你也好歹替我糊弄一下,这就看你小子的本事啦。今晚,我将乘三等末班火车去东京,明天早晨赶头班车回来,拜托啦。”
“好吧!”
本多响亮地接受下来,清显满怀幸福地伸出手和本多握手,接着进一步说道:
“有栖川宫殿下的国葬,令尊也会出席的吧?”
“嗯,看来有可能。”
“他死得正是时候,昨天听说,因为他的辞世,洞院宫家的纳彩仪式也要延期了。”
本多从这位朋友的话里,得知清显的恋爱一一关系着国事,再次切切实实感到一种危险。
这时,王子们高高兴兴手拉手奔跑过来,打断了他俩的谈话。库利沙达气喘吁吁,他用稚拙的日语说道:
“刚才我和乔培说些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谈了转生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