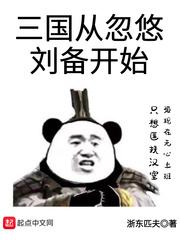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她死遁了 第1章 > 第269章 丧权辱国(第2页)
第269章 丧权辱国(第2页)
去年连城最胆颤心惊的时候,薄颐章这三个字,一度成为她梦魇。
梦里闻名全国的妇科圣手,长得仙风道骨,眼睛却是纯黑色,无一丝眼白。梁文菲一出现,他眉心又长出一弯黑月亮。
施展了把脉孕相的基本功,立刻惊堂木一拍,喝她下跪,“大胆荡妇,你竟敢怀孕。”
连城双目苍凉又衰颓,死咬不跪,梁文菲当先跪下,抬手仰望苍天,“青天大老爷。”
这会儿一见,对方头发茂密黑浓,六十多岁眼睛依旧黑白分明,着装却很朴素,有过去文青的拗劲,又很儒雅。
梁朝肃刚起身,他小跑过来,说不出的感激和愧疚,“抱歉梁董,我应该提前看过天气预报,早一点出门的,实在不好意思让您等我这么久。”
梁朝肃握住他手,晃了晃,松开,“天气是不可控因素,薄先生不用在意。”
他望向连城,简单介绍寒暄过,就让她伸手,便于薄颐章诊脉。
连城伸手。
她如今没有身孕,也不是年前对梁朝肃老鼠见猫的时候,没必要犟着,惹出变故。
是以,诊脉是商量好的。
“她的情况,我之前告诉过你。”梁朝肃凝望连城脸颊,“虽然上次体检,贫血有好转,但脸上依旧没有血色,前几日上火烂过嘴角,平常手心也很凉。”
薄颐章搭上连城手腕,颔首静默片刻,抬眼慎重注视她面庞。
梁朝肃看出不对,又怕出声打扰薄颐章诊脉,垂在身侧的手攥成了拳头,松了紧,紧了松,胸膛绷成一块巨石。
连城被瞧的不自在,“我不治不孕。”
薄颐章凝目,斟酌片刻,问了个最轻的问题,“夫人最近有没有发过高烧?”
梁朝肃脸色一沉,声音又冷又急,比连城快一步,“不到高烧,体温最高一次三十七度九,吃了药,反反复复一天半恢复正常体温。”
话落,薄颐章神情更凝重,让连城换手,再问,“夜里睡眠怎么样?”
不待连城回答,他补充,“连续超过三个小时,或是深度睡眠。”
连城心底一松。
从去年到现在,事多杂乱,一桩接一桩,全是要命的紧迫。她晚上闭上眼,脑筋却没有休息,复盘细节,关紧,串联线索。
睡着也像没睡着,清晰知道自己在思考,总之,昏昏沉沉熬过一宿,不影响第二天精神清醒,紧绷。
“我最近睡眠很好。”她说,“在行车途中也能睡得着,虽然短暂,但入睡程度很深,昨晚更是一觉到天亮。”
薄颐章皱眉思忖,“饮食呢,有没有味觉,食欲强不强。”
外面风雨沉晦,室内灯光全开了。暖黄的,米白的,光影并不刺目。
梁朝肃过山车似得,只觉混乱,飘忽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她年前丧失过味觉,跟远东医药爆出问题的那种针剂有关。”
薄颐章知道这点,他问的是当下。
“有味觉,我一向吃得少。”
连城抿了抿唇,直率问,“是我有什么问题吗?”
“素体不足、真阴亏虚、瘀毒阻络、内侵脏腑。”薄颐章只说脉象,“从年后到现在,您除了嘴角,还有其他皮肤损伤吗,比如起红斑,或红疹,对光过敏,口腔溃疡之类?”
连城完全放心了,摇头,“没有。”
梁朝肃看向薄颐章,他耷拉着眼皮,深思熟虑的模样。
梁朝肃眉头皱的死紧,焦躁和担忧,极力克制压抑着。
薄颐章不出声一秒,他手臂筋脉绷鼓一秒,像岩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喷发。
薄颐章终于起身,“梁董,可否借一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