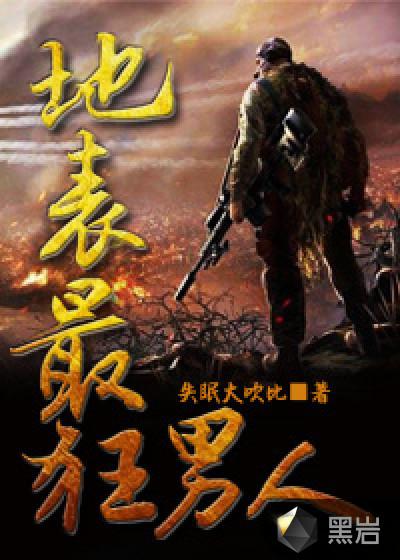456小说网>澹月微迟番外免费阅读 > 第52章 我真的很担心你(第2页)
第52章 我真的很担心你(第2页)
紧接着,是那堆放在箱子角落里,一幅又一幅的卷轴。
她将它们搬出来,徐徐展开。画上,全都是同一个人。
荡秋千的,糖葫芦吃得满嘴都是的,巧笑嫣然的,扑蝴蝶的,六岁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十五岁,到十六岁,戛然而止。
每一岁,都有一幅画。
十六岁的少女,身穿嫁衣,立在无边的荞麦花田中回眸微笑。
她们或嗔或笑,或坐或立,那样生动,那样鲜活,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模样么?在那些她不曾在的年岁里,在他以为她已逝去的年岁里。幻想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幻想着她穿着嫁衣,走向了他。
她想起江从安对她说,“每到特定的日子,官家便会来这里枯坐。一坐便是一宿。年年如此。”
她将最后一幅,缓缓打开,不知为何,手腕有些轻颤。
画上不再是巧笑嫣然的少女,而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荒野中,是坟墓。
就在那座小小的坟墓旁,有一座半人高的坟冢。
同样无字无碑,与那座小小坟墓依偎在一起,仿佛最亲密的爱人。那碧落黄泉终不见的空寂萧瑟从画中挣出,一瞬袭来。
啪嗒,一滴眼泪打湿了画纸。
她指腹轻轻抚上,心脏抽痛,那夜新婚她问他,倘若将来有一天,她先他而去……他的答案,原来早就藏在了这里。
她对着空气喃喃,“你是想在什么时候,来见我呢?”
却不知何时,他也走了进来,悄然地站在她身后,回应她,“大庆足够强盛,物色一个足够优秀的继承人。母后想要独揽朝政,那便遂了她的心意吧。反正这么多年,我过得很累,也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做你的小和尚。”
他是破碎的,唯有遇到她才完整。
“我有什么好呢?”她做的小笼包那么难吃。她还动不动就哭鼻子。
仗着他喜欢她就蹬鼻子上脸,恃宠而骄,还抓花了他的背。
她想破了脑袋,都没想出自己有哪里不同于其他女子的地方。
“你比所有人都好。”施探微阖着双眸,低低地说,“你同情世间所有女子,愿意为了毫不相干的人以身犯险。归云岭之行,你救了那么多人。你的功劳,封侯拜相都值得。你想做什么,都一定可以做成。你想开食肆,一定能经营得有声有色。是我如此自私,要将你困在我的身边。”
一起再看胡旋舞时他便知道,她还是她。
那个向往着自由快乐无忧无虑的她。还是多年前看着他的眼睛,发出赞叹和钦赏的她。
“不,不要自责。这里不是牢笼,因为有你在。”迟迟扑进他的怀中,捧起他的脸,“有了你,这里就是我的家。”
她哽咽着,“是我们的家。”
“嗯。”
“如果我一直没来。这些画,你打算……画到多少岁?”
她已经泪流满面。
“到我画不动了为止。”也算是守着她长大了吧,那个小小的她,终于也可以长大了。
他擦去她的眼泪,“你放心,如果你没有来,我大约与这世上的凡夫俗子一般。有了喜怒哀乐之事,娶妻纳妾,儿孙满堂。只是,永不会再有一人为我喜而喜,为我悲而悲。因为我是施探微而拥抱我。”
骗子。
迟迟在看到那两座坟墓时便已经知道了,他不是这么想的。
他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过留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