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小说网>四月间事电视剧什么时候开机拍? > 第11章(第3页)
第11章(第3页)
卫来不吭声了,提这个要求有点得陇望蜀的感觉,怪害臊的——都多少年没害过臊了?
“那你现在对我什么看法?”
“我想一下。”
他没想多久:“我觉得你挺没劲。但这个没劲吧,又不是大家都觉得的那个意思。”
卫来斟酌着怎么说最合适。
“我在拉普兰,遇到过一个萨米族老头,他请我进帐篷烤火,聊天的时候,他说,人的一辈子,像根烧火的木柴。”
“开始是树,要生长。长成了,就是砍下来的柴。”
“做事、工作了,就是柴燃起了火,发光,发热,一身的劲。”
“最后老了,就是烧完的柴,成了炭块,渐渐凉了。”
“岑小姐,你像块正在凉的炭块一样。”
“你跟沙特人讨价还价、跟我说话、签约,乃至去烧姜珉衣服的时候,你的情绪,都是一样的。”
像最平的旋律,没有起伏,不知道这只是前奏呢,还是通贯全篇。
岑今说:“我这个人,确实很无趣。不止一个人这么说了。”
她往下躺了躺,帽子拉上:“这一路,你如果觉得无聊,保证我安全的情况下,尽可以出去找乐子,我不会向沙特人打报告的。”
说完阖上眼睛。
最糟糕的旅行同伴,就是你一路开车,她一路睡觉。
真可惜,一张漂亮的脸,搭了这么个无趣的性子。
卫来尽量往好处安慰自己:无趣只会让同伴觉得无聊,总比强行有趣把人逼疯来得好。
他只当是一个人开车夜游,兜风。
风撼动高处尖尖的黑色的树梢。
大河像夜色里弯曲的镜面,里头落着被冻瘦的星星。
终于驶进图尔库小城的时候,路边的草坪上蹲了个巨大的充气鸭子,像在孵蛋。
***
塔皮欧大概是油码头的“名人”,卫来问了个夜班的工人,很快就找到他的单人宿舍兼值班室。
时间已过半夜,他房间还亮着灯,门半掩。
推开门,塔皮欧诧异地抬头,他五十来岁,满脸乱蓬蓬金色胡子,捧一本色-情杂志,手边摊开的快餐纸盒里都是薯条,番茄酱挤得一滩一滩,像不新鲜的血浆。
他油腻腻的手接过卫来的“船票”,恍然大悟一样:“哦,沙特人的路子。”
钱是沙特人的脸,全世界都给面子。
塔皮欧搓着手,翻看边上破烂的登记本:“你们来的有点不巧……好几艘货轮都刚走……倒是还有一班船……从立陶宛出发,要去德国的,海上遇到风暴,迷了航,在图尔库停了好几天。马上就要开了,我应该能让你们上,但是……”
他忽然压低声音,凑到卫来耳边,带来好大一股夹薯条啤酒的狐臭味。
卫来闭气。
“但是,你们上船之后,必须一直待在房间里。不管看到、听到什么,都不要管,不要问。到了斯德哥尔摩,下船就是。”
懂了,是黑船。
卫来皱眉:“还有别的船吗?”
“有是有……得等,最早的一班,还要四个小时。”
卫来回头,看倚在门口的岑今。
她脸色疲倦,犯困,语气有点不耐烦:“既然现在有船,就走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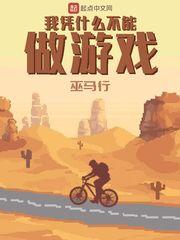

![营业悖论[娱乐圈]](/img/3715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