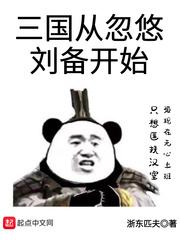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恨春光易老的词 > 第四百一十五章 赤诚(第1页)
第四百一十五章 赤诚(第1页)
濯龙园在南宫的东北角,园子极大,景色秀美,正中有一座九华宫,是南宫里最大的一间宫殿。
平日的濯龙园,外男禁入,今日太子大婚,破例开放。
此刻,树上挂满红灯笼,地上铺满红绸,一眼望去,深重的绿和艳丽的红交相辉映,喜气极了。
溶月被秦长风搂着,踏上九华殿前的高阶时,天空飘起细雪,秦长风忽而顿步,拉着她眺望雪色。
“还记得江家的夜宴吗?”
“恩?”
“那日也是飞雪漫天,顽顽抱着一张柳琴,孤身坐在龙舟,为金陵权贵,弹了一曲《阳春白雪》。
那一曲甚美,美到让某生出一念,来日定要让顽顽夜夜弹一曲,谁知此去经年,此念依旧是念。”
秦长风话里的怨念听得溶月忍俊不禁。
“殿下记得真清楚。”
“关于顽顽的事,某一向记得清楚。”秦长风身子一转,有些生气地说,“不像顽顽,总是忽略某。”
她忽略他?
过去或许是,可自从她追来大兴,什么时候不是以他为先了?!
“秦溪辞,我们才成婚,你就和我翻旧账?”
“成了婚才敢翻,不然,某怕你又跑了。”
溶月笑了,她伸手勾住秦长风的手:“父皇和百官都进去了,我们还不进去吗?”
“不急。”秦长风拢紧她身上的鹤氅,“某更想和顽顽说说琵琶的事。”
“……”
“不能说?”
“不是。”溶月又笑,“其实,我不爱弹琵琶。”
“因为琵琶不够雅?”
“当然不是。”
不雅的从来不是琵琶,而是她卖笑的半生,那是她永远不想、不愿、不能提及的半生,但——
溶月抬眸。
夜雪下的秦长风,眉目如画,清冷如仙,这样的人不仅和她生了情,还为了这段情,九死一生。
他的心是如此的炽热,真诚,不像她,蒙着一层厚纱。
也许,她该掀了这层纱。
“溪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
她轻瞟四下,见奴婢们都站得很远,才张开嘴,轻轻说:“这场人生我走过两次,上一次——”
“嘘。”秦长风伸出一指,封住她的唇,“某知道。”
“知道?”溶月有些茫然,“殿下知道什么?”
秦长风没有正面回答,他搂紧溶月,目光落下遥远的东方:“顽顽记得张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