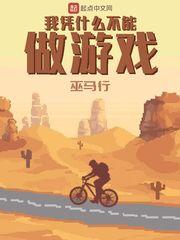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恨春光免费阅读 > 第六十一章 熟人(第2页)
第六十一章 熟人(第2页)
“恩。”
等溶月穿戴妥当,坐到梳妆台前,她看见倒映在铜镜里的林缨还没回过神,她脸色一沉,冷声问:
“怎么?”
“没。”
有些事,她无需告诉林缨。
但,秦长风是个喜怒无常,又难以预估的人,谁晓得,下一回他会在什么时候又出现在她房里?
林缨是她的贴身婢子,一两次撞不上,却不可能次次撞不上,与其撞上得惊慌失措,不如现在就告诉她。
“姑娘,奴婢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问。”
“既姑娘和秦三殿下有情,那为何——”
“谁告诉你我们有情了?”
“欸?”
“你既在咸宜观待过,便该晓得,第一,情和欲是两桩毫不相干的事,第二,男人的情一文不值。”
说罢,溶月走出里间,待她瞥见廊下的巧慧,立刻回身告诫林缨:“收起你的错愕,别叫人看出端倪。”
一到廊下,巧慧驱步到溶月跟前:
“婢子见过月姑娘。”
“劳嬷嬷久等。”
“姑娘这话说得,真真是折煞奴婢了。莫说奴婢只等了一时片刻,便是等上三五日,那也是本分。”
巧慧朝廊下招手,几个仆役抬过来一张辇轿:“姑娘,地上积雪甚厚,老夫人让人抬着姑娘去兰雪台。”
“多谢外祖母。”
“这话啊,明早上姑娘自给儿同老夫人说去。”巧慧笑盈盈地扶住溶月胳膊,“奴婢扶姑娘上辇轿。”
“房里还有些东西没收。”
“月姑娘放心,自有人收,便没人收,去了兰雪台,也是什么都不缺的。”
“好。”
溶月坐上辇轿,出了院门。
路过添眉苑前,她瞥见四舅母披着斗篷慌慌张张地冲出门,但,没等她冲上来,轿子已被抬出许多远。
远远地,她看到兰雪台的院门大敞,墙上爬得乱七八糟的藤曼被人扒了个精光,奴仆埋在雪地,忙着修整院落。
巧慧跟在辇轿一侧,笑言:
“老夫人说,这会儿天冷,万物冬藏,不便移栽草木,等开了春,再叫人好好整一整兰雪台的院子。”
“停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