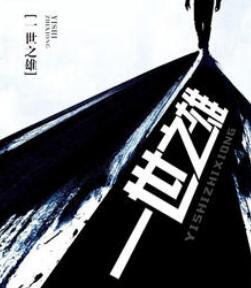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恨春光免费阅读 > 第八十七章 天晴(第2页)
第八十七章 天晴(第2页)
“是我。”
止水这才拢上衣衫:“婢子给姑娘请安。”
溶月不说话,径自走到止水身前,扯开她的衣襟。
她的身上,鞭伤纵横交错,新伤叠着旧伤,可怖到触目惊心。
林缨挨不住,红着眼哭了一声,溶月也觉得难受,止水却不甚在意地笑了一声:“姑娘,婢子没事。”
怎可能没事?
她身陷长春馆十余年,也曾挨过鞭子,最多挨上三鞭,她就受不了了,可止水挨过的鞭子数也数不清。
她究竟经历过什么?
“林缨,去把我房里的伤药拿来。”
“是。”
“还有,把雪花生肌膏也拿来。”
“是。”
林缨飞快而去,她一出门,止水又一次拢上衣衫:“姑娘,婢子身子卑贱,用不上雪花生肌膏。”
“再卑贱,也是女子。”
止水闻言,心头一乱。
成为影卫的头一日,首领告诉她,影卫只有强弱,没有男女,若她妄想有人能因为她是女子而手下留情,那她必定死得比谁都快!
她也早忘了自己是个女子。
“为什么要任由江家刑讯逼供?为什么宁愿被打也不招供?”
她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江家逼供的手段不入流,不足以叫她说出实话?
林缨复又奔进门:“姑娘,药取来了。”
“替止水上药。”
林缨上前,要替止水上药,止水却惊得连连后退:“不必,我自己来。”
“那不行,姑娘的命令不可违,你得乖乖让我上药。”
“不——”
“不许不行,不然,我不理你了!”
明明是一句威胁的话,却被林缨说得可怜巴巴,约莫是听着太可怜,止水不再挣扎,由着林缨替她上药。
不知不觉,风雪停了,夕阳的余辉照上回廊,美得叫人心颤。
溶月靠在门边,看林缨笨手笨脚地替止水上药,唇角不自觉地勾出三分笑意,果然有人相伴,日子才过得更有意思。
不一会儿,止水忍无可忍,夺过药罐子:“你是上药,还是杀人?”
“怎么了嘛?”
“疼!”
“你——”林缨扭头,气得冲到溶月跟前,“姑娘,您瞧瞧她,真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溶月失笑:“回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