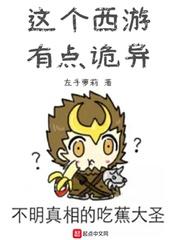456小说网>霍去病的主要事迹 > 第十三回(第1页)
第十三回(第1页)
很早以前,在匈奴这个游牧部落里,丧葬有棺椁、金银和衣裘,但却不堆坟种树,祭奠死者的人也不穿丧服。但撑犁孤涂大单于死后,他所亲近和宠幸的大臣、妻妾跟随陪葬的多至数百人。几个辅政王侯并没有在为选谁陪葬的问题上大伤脑筋,他们最为头痛的是撑犁孤涂大单于最终没有留下遗诏,明确把王位传给谁。
从军臣单于咽气的那一刻起,王庭空气中的火药味骤然增浓。对于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大家各怀私心,为自己的贵族地位和前途打算。以左骨都侯也里哲等辅政大臣为一派的保守派,主张按照祖制,让王子於单继承大单于王位。因为阿鲁骨已死,军臣单于仅此一个王子,於单理所当然继承大统。这一派的骨干大臣有左右贤王、左右骨都侯、阏氏等人。以藉若侯产等统兵外将为一派的激进革新派,主张拥立左谷蠡王伊稚斜继承大单于王位,理由是於单的阿妈南虑公主是个汉人,於单的身上流着一半汉人的血,撑犁孤涂大单于的王位必须由一个纯正的挛鞮氏血统来继承。这一派的支持权臣有左大将、右大将、左大都尉、右大都尉、左大当户、右大当户等人。双方围绕撑犁孤涂大单于的继承人问题争得不亦乐乎,大有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之势。
工于心计的也里哲,觉得再这样争执下去必然引起匈奴内部的大乱。
这个须卜氏人中的智者,主张先安葬军臣单于,后议王位人选。
也里哲依照匈奴的风俗,让军臣在王庭停尸数天,也里哲、於单等人在军臣单于的尸体前一直守灵。他们的眼睛红肿了,嗓子哑了,压低了声音哭泣。匈奴人的风俗是不能在死尸前放声大哭,怕活人的阳气冲散了撑犁孤涂大单于的魂魄。
军臣单于的灵位前放着一张桌几,摆满了煮熟的牛头、羊头、糌粑、青稞酒等祭品,一盏酥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挂了白绫的毡帐显得鬼气森森。停尸的帐外有执刀的卫士把守,不许女人和孩子大声喊叫,更不许发出笑声;不许在灵帐附近剁劈木柴、发出声响;不许猫、狗等动物接近灵帐周围,以免借尸还魂。
在停尸的最后三天里,也里哲召集了匈奴所有的萨满,念着《神狼》的经文,超度亡灵。
一位瘸腿的萨满往军臣单于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上抹了一层新鲜的酥油,也里哲撬开军臣紧闭的嘴,让他含了一颗西域龟兹国国王朝贡的夜明珠。这颗夜明珠用珍贵的天山于阗翡翠玉琢磨而成,玲珑圆润,色泽暗绿,价值连城。
在也里哲的指挥下,几名老萨满用白布把军臣单于尸体的腿部膝关节和胳膊肘关节收拢捆住,让他双手贴耳呈弯曲状,然后将尸体装进一个用一丈五尺羊皮缝成的口袋,用五色彩绳将布袋口扎住,将羊皮袋口多余的部分从上翻下来。一名武士抽刀剁下了一只扑棱棱抖动翅膀的雪鸡的脑袋,将喷涌的鸡血滴在一只酒碗里。也里哲饮完满满一碗鸡血酒后,用墨块在羊皮袋上画了一只展翅的雄鹰,然后,把捆成聚宝瓶状的尸袋装进棺椁里。棺椁里陪葬的除军臣单于生前用过的镶有猫眼宝石的长柄腰刀、弓弩外,还有大量的金银酒器。
黄昏时分,老北风停止了呼啸,冬阳的余晖在空寂的野外渐渐隐去。身着裘皮的於单指挥着王庭的数千骑兵,将数百名用来给撑犁孤涂大单于陪葬的男女老幼,像驱逐猪狗一样用鞭子赶往墓地。这数百人大多数是军臣单于生前亲近和宠幸的侍女以及已经不能骑马的老臣,还有一部分奴隶和战俘。赶往墓地前,於单强行让他们吞食了生长在肯特山的哑草,吃完哑草的叶子,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成了哑巴。那哑草生长在肯特山阴面的山坡上,夏季开黄花,枝叶扶疏,有二尺高,花籽可入药,医治败血症。数百名说不出话来的陪葬活人,泪流满面,在鞭子啪啪的笞打声中,大张着口,哇哇呀呀一步一趔趄地被赶往军臣单于的墓地。
出殡选在五更天。
夜深人静,冷月如钩,肯特山错落有致的树林和峰峦显得阴森恐怖。地上积着一层厚厚的冰霜,几名身强力壮的骑兵抬着棺椁缓缓前行。
被软禁的火绒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戴着狐狸皮护套的双手握住鱼状的胡笳呜呜地吹。
送葬的人马穿过结冰的图拉河,出了博格多山的南口,向肯特山山谷走去。凄怆悲凉的胡笳乐声在寒冷的冬夜呜呜地飘荡,让所有送葬的人马备感凄凉与悲切。
由于伊稚斜远在河西,左骨都侯也里哲征求於单王子的意见后,让被软禁的火绒代替她的阿爸给大阿爸军臣单于送葬。由于火绒胡笳吹奏的水平极高,就让她担任送葬的引魂乐手。火绒吹奏的《野狼长调》,是匈奴人殡葬时专门给死者引魂的音乐。呜呜的胡笳声,在夜深人静的五更天,更显得无限悲凉。脚步下的薄冰,被踩得咯吱咯吱直响。
为了给军臣单于选好墓地,也里哲踏遍了博格多山和肯特山附近的山峦、沟壑和森林,终于选定了一座山峁。这座山峁对岸有一山峁似平案,案左山峦如鹰,案右有一山丘像鹿,山峁的背面有两座不大不小的圆峁子石山,一座似鼓,一座如旗。
这是阴宅的极佳风水宝地,曾经跟随陪同公主和亲出塞的未央宫宫监中行说学习过几年汉家周易风水的也里哲立即选定了这面山坡。
墓穴很大,等骑兵将棺椁放好后,於单指挥王庭卫士一脚一个,将那些陪葬的男女老幼全踢进了墓坑,有些身强力壮的男子还想挣扎着往上爬,立即被骑兵一刀砍倒。
也里哲手执一根干枯的芦苇花,一边端着酒碗敬天地,一边开始念经。在他嘤嘤嗡嗡蚊子一样的念经声里,泥土将棺椁和陪葬的活人全部掩埋……
处理完军臣单于的宾天后事,於单便和也里哲一起率领王庭的数万骑兵,团团围住了藉若侯产驻扎在图拉河畔的屯兵营地。
这个冬天冷得邪乎,凛冽的北风能把山坡上的石头吹裂。豪华的穹庐里,干瘦的藉若侯正同来自河西五属国的都尉、当户等人围着巨大的炭盆烤火饮酒。穹庐旁,一堆熊熊烈火上正架着一只刚刚宰杀的羊羔在炙烤。这种羊羔在肯特山附近叫“青口羊”,专门供给匈奴的王公贵胄们享用。据说这种羊羔出生后,靠喝母羊的奶、吃河边的嫩草生长,肉嫩味鲜,烤熟后连骨头也可以嚼碎。
一个负责烤肉的驼背老人正跪在地上摇着烤肉轮子精心地烤着那只鲜嫩的羊羔,还不时地往半生不熟的羊羔肉上撒些盐巴、胡椒粉之类的作料。
老人看上去有六十岁左右,两鬓斑白,一脸烟火气,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只知道干活。
在穹庐阔大的厅堂里,由马头琴、胡笳、唢呐、大铜角、牧笛等乐器演奏的胡乐《清泉水》正在回响。在舒缓而优美的音乐声中,一个身着白色狐狸毛沿边袍子的匈奴少女翩翩起舞。少女那两条柔若无骨的胳膊忽而舞作鹰在万里草原飞翔的姿态,忽而又舞作小河流水的姿态,那微微耸起的小巧匀称的鼻翼显得非常可爱。
藉若侯撕咬着半只烤得焦黄酥香的羊腿,色眯眯地盯着少女迷人的舞姿哈哈大笑。
“藉若侯,”一个来自哨卡的候骑急急入帐来报,“左骨都侯也里哲和於单王子兵分三路把我们团团包围了!”
藉若侯正举着酒碗同属下诸将军校尉碰杯,听了探马的禀报,心中一惊,却不动声色地说:“再探。”然后,继续与左右饮酒作乐。须臾,又一名候骑来报:“侯爷,左骨都侯的先锋骑兵距此只有二十里。”那个流星探马说毕,退出穹庐。藉若侯脱口一个“喝!”便先将一碗酒喝了。他喝完酒,捋了捋他的山羊胡子,厉声道:“弟兄们,匈奴有一句俗话叫‘宁为屠刀,不做羔羊’,撑犁孤涂大单于刚刚宾天,有人就要向我们左谷蠡王的人马下毒手了。”大家听了义愤填膺,乱纷纷地嚷道:“藉若侯,我们听你的!”藉若侯一张山羊一样的瘦脸往前凑了凑,鼻子越发像鹰的喙钩一样,他冷冷地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还击,只有杀开一条血路,我们才有生还的可能。”顿了顿,这个历经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的干瘦老头,凭着娴熟的作战经验,迅速做了军事部署:“左右大将挥师北上,抵御锐气正炽的左骨都侯;左右大都尉挥师南下,同於单的人马作战;左右大当户随同我从侧翼突击。三日后,所有河西人马在图拉河下游集结。”
河西的左右大将率领数千精锐骑兵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挥师北上,在肯特山左侧中了左骨都侯先锋骑兵射手的埋伏。当左右大将率领人马,杀气腾腾冲过来,王庭的左骨都侯咧嘴嘲弄地笑了笑,便弯弓搭上一支鸣镝,向左右大将的突围骑兵射去。随着那支响箭呼啸着射入敌阵,数千名马上弓箭手,顿时弯弓搭箭,齐齐地射了过去,箭矢如雨,猝不及防的骑兵便一个个从飞奔的马匹上栽了下来。有的箭射中了马头,战马驮着骑手一同栽倒。
箭雨一歇,又有数千挥动着鬼头弯刀的兵甲,骑着快马飞也似的迎了上去。
双方人马战在一处,约莫两个时辰的工夫,河西五属国的左右大将和麾下骑兵全部战死疆场。
南下的左右大都尉正好碰上王子於单的人马。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於单仗着人多,把只有数千人的河西兵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左右大都尉再怎么冲也无济于事,最后在激烈的血肉鏖战中做了於单的刀下之鬼。
藉若侯产的人马从侧翼突围的时候,正好碰上老谋深算的左骨都侯也里哲。
两军对垒。
“藉若侯,”白须飘胸的也里哲精神矍铄地坐在马上,以鞭遥指藉若侯道,“离了群的孤羊迟早都是狼的口粮,下马受降吧,免得我们匈奴人骨肉相残!”
“哈哈哈……”藉若侯在马上哈哈大笑,“狮子没项圈抖不起威风,马儿没鬃毛扎不起势力!也里哲,撑犁孤涂大单于已经宾天,真正能统驭匈奴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左谷蠡王伊稚斜。你堂堂一个摄政侯,竟然为於单这个汉家女人所生的牦牛犊子卖命,实在是可笑!”
“落在陷阱的野狼,能逃出猎人的手掌心吗?你大概忘了自己的危险吧?”也里哲冷冷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