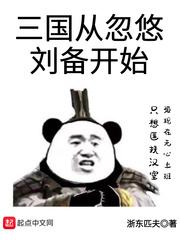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听雨txt > 第114章(第2页)
第114章(第2页)
虽说戏台宽敞,但台下座次倒是颇为野趣,没有像一些酒肆茶坊中将位置分作观客的包厢与普通百姓,这里哪怕是“为他们提前准备”的位置,也不过是前排一摞长而窄的木板凳,就像是乡间戏台一般。
那礼部尚书是个长相瘦削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四五十岁,相貌并不堂堂,却很是书生气,见到几人,也十分客气,几人落座后,他小声开口介绍:“方才先演的是《目连救母》,已快演完了,待会要上的是泉祥班,哦,就是我们这戏最好的戏班子的名字,他们要排《钟馗捉鬼》,这一出班主已经筹备许久,可是要明年进京演给皇上看的!”
若是陪都位下的戏班得了好,他作为陪都的礼部尚书,自然也能得些青眼,因而提起泉祥班,礼部尚书语气里也带着些自豪。
话中,《目连救母》已演到了末尾,周遭百姓大声呼好:“好!演得好!再来一场!”
很快,《钟馗捉鬼》中的一神一鬼便从幕后走出。这一出戏目倒是与前头的《目连救母》有所不同,打扮英武的钟馗与一身灰袍甲胄的鬼脸上,都各挂着一块漆彩的木制面具,这是先古“驱傩”仪式中会出现的典型造型。这迥别的形象,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场百姓,现场喊叫纷纷息了下来。
甫一出场,浑身赤色的钟馗手持长枪,大喝一声,便灵便地打了好几个跟头,叫百姓啧啧称好,那木头鬼脸似是一怔,抬手格挡,方也翻身躲避,几个漂亮的一击一挡功夫下来,引得满堂喝彩。
“不愧是泉祥班,这功夫底子可真好!”司若听到他旁边一个百姓拍手道。
另一个百姓颇为自豪地回道:“你不看看演钟馗的是谁!那可是‘叫破天’!谁不知道叫破天是泉祥班的台柱子,也就是今时今日咱们能免费看叫破天老板演戏,往时还不知要花多少银子呢!”
那百姓连连点头:“可不是,可不是!泉祥班就叫破天赚钱,听说旁的那些个角色,每每登台,收到的礼不如叫破天十之有一,怪不得班主这样喜欢叫破天呢!”……
司若其实没有多喜欢看戏,戏台总在人群之中,他不喜人群,因而并没有多少注意力放在戏文之上,反而是听到了不少台上台下的风月消息。但他向来又是个一心二用的高手,看着这台上钟馗与鬼的对戏,与台下反馈,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
台上,钟馗目光如炬,左手翻了个跟头,右手紧持长枪,朝木头鬼脸刺去:“看逮——恶鬼,你还要往哪里去,不如归我往生天——”他枪枪向前,如同破空,尖亮枪头划过空气,发出嘶嘶的锐响。
“我不过一朝入鬼道,何必纠缠我入万劫不复门——”那鬼躲闪着紧追枪法,似乎有些吃力,但口中仍念着唱词。
司若忍不住皱眉,扯了扯身边沈灼怀的衣袖,小小声道:“沈灼怀,你觉不觉得……这钟馗对鬼的恨意,有些太像真的了?”
沈灼怀看这样的戏不算少,因而也没有很沉迷,倒是时时注意着司若,听他这样说,一愣,也细细观察一番:“……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如此。”
也不知是不是他们多想,那钟馗招招朝着鬼致命处去——但既是要演给皇上看的本子,自然也要使出最大功夫,这么做倒也没错。只是司若总是对那恨意敏感一些,他总觉得哪怕是排戏,钟馗眼中对鬼的恨似乎也犹如实体……这台柱子叫破天与一个搭戏的演员,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正在司若思索之时,台上已演到最精彩时刻——钟馗收鬼入囊。
只见二人又是慢动作对立一番,钟馗高喝一声:“恶鬼,哪里跑,看我锦囊!”,便一枪直直冲出。然而这一次,鬼没有再躲开钟馗的攻击,“噗嗤”一声闷响,长枪尖端插入恶鬼喉头,钟馗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连唱三句戏文,而后用力一挑——
竟将恶鬼用一条长枪挑在半空!
“好!”
“太好了,演得太好了!”
“叫破天这功夫真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啊!”
百姓们大声叫好,众口交赞,钟馗似是也觉得有些累了,一把将长枪收回,那鬼大叫一声,浑然倒地,一动不动,而钟馗则面对百姓,抱拳感谢。
“今天这鬼演得也比昨天好多了!”一个百姓喜笑颜开,“这一场真是来对了啊!”
但恶鬼倒地,翻转几下,正面对准了观众台前,却叫司若发现了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