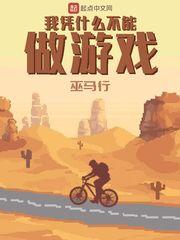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姑娘千娇百媚 > 第56章 前尘往事(第2页)
第56章 前尘往事(第2页)
她那年才十一二岁,田间干完活回家路上,被几个兵痞拖到废窑里轮番欺凌了。
孙姑娘破了身子,求告无门,寻死未成,是以性情大变,索性破罐破摔,做起了暗门子。
年轻的姑娘,花骨朵一样的身子,镇上一些没娶上媳妇的光棍儿、鳏夫、地痞无赖,都是她的入幕之宾。
“她爹找到铺上,哭着求我给打具薄棺材。我说不用钱,送她一副厚实的好材,那姑娘活着净受罪,死了躺得舒坦些,下辈子投个好胎。”
“官府衙门怎么定案的?”她声音清浅,像山巅融化的雪水,不含杂质又透着微冷。
“一个末等流民,死了都不用偿命,还能怎地?这世道真是造孽啊。”
大乾朝廷将治下子民按高低贵贱分成五等,被灭国、后来归附和小部族的都纳入末等民,地位在囚犯和官妓之下。
对这些外族,不但横征暴敛,还动辄严刑酷法打杀,甚至一等民无故打死末等民都无须偿命,是以各地揭竿而起、战乱不休。
从晌午忙到子夜,到底是有几分疲累了。
她有些慵懒地倚坐着,拿起一旁的酒壶,纤指弹开壶塞,仰首喝了一大口,神情似带着些许微醺的迷醉。
朦胧见,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
窗外吹进的夜风带着湿意,撩起她耳边黑丝缎般漾着柔光的长发,愈发衬得肤白如雪,由内而外泛着微微的白瓷釉光。
“按说原本咱这开棺材铺子的,煞气重、触眉头,是个大凶之地。”
“初来乍到时,店铺都得避开闹市,找这么个荒僻的地界儿开。寻常人嫌晦气都绕着走,谁爱没事上门来扯闲篇。”
“可偏有人三天两头寻出各种因由往这跑,也不怕犯忌讳,你说,这是为啥?”萍娘别有深意地挑起眼尾,“是姑娘手艺巧夺天工?咱家棺材做得好看?”
羽昕把着酒壶,小口小口地啜饮。暖黄的烛光下,深潭般的眼眸半明半暗,神色喜怒不辨。
萍娘微微倾下身,在她耳边压低了声音,“孙姑娘一朝殒命,那事儿也跟着带到地底下去了,我这悬着的心总算落放了。不知是什么人做在了前头,手段虽刻毒了些,倒也省着脏污了咱们的手。”
“此番能逃出生天实属不易,这条命是记在阎王爷账上的,说不准什么时候要讨回去。你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当知道往后要怎么活,如何活下去。”
“跟命比起来,前尘往事俱不足道。打今儿个起,把那些子事从心里,脑子里抠干净了,莫要去念着半分。”
见玥尘白得仿若透明的脸上,如古井般平静无波,也不知这话听没听进去。
咽下了唇边的叹息,萍娘缓步踱到窗边,“这棺材铺的生意眼下还好,但你我终归女流之辈,日子久了难免闲言碎语,徒惹麻烦。”
两个美貌的妇人撑持这棺材铺,少不得镇上的地痞无赖、酒鬼赌徒上门来寻麻烦。
“孙姑娘殷鉴不远。无根无基的外乡人,家里一日没个顶门立户的爷们,这日子便消停不了。”
羽昕嘴角一抿,露出浅浅一笑,唇边两个梨涡如两朵花苞绽开。
“若是萍娘有了意中人,我定备一份厚厚的嫁妆,送萍娘风风光光出门子。便是招婿入赘,也未尝不可,我必当以父礼待之。”
萍娘听罢,啐了一口,“你当我是跟你逗闷子呢?我都这把年纪的老太婆了,你也能拿我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