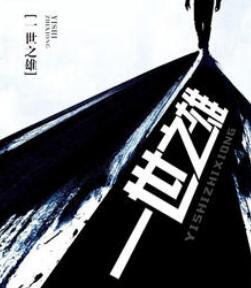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掌事女官清穿格格党 > 第129章(第2页)
第129章(第2页)
性于她而言,曾是很令人愉快的消遣,如果要成为将她锁起来的牢笼,那活着有什么意思?
陈嬷嬷没办法回答耿舒宁的问题,无声叹了口气劝。
“这世道女子不都是如此?您实在没必要跟万岁爷较这口气儿。”
“起码万岁爷对您上心,金尊玉贵地活着,已经比大多数女子要强了。”
耿舒宁撑着额头,扯了扯唇角。
“我心里有数,明儿就跟万岁爷陈情,嬷嬷放心吧。”
她无法叫陈嬷嬷明白,不管在哪个世道活着,她都少不了这口心气儿。
上辈子她没了亲人,在这里也如浮萍,想好好活着,凭的就是那口气儿。
没了心气儿,也许去地下跟奶奶团聚还更好些。
*
翌日一大早,耿舒宁请陈嬷嬷给御前递了一封信。
苏培盛战战兢兢将信送到主子手里。
胤禛从昨夜起就憋着一股子气,说不上恼火,就是有些厌烦耿舒宁这些小伎俩了。
不过一个女人,愿意伺候就留着,不愿意就关去庄子上,暗卫有千百种法子,能叫她把肚子里的坏水儿吐干净。
面无表情打开信笺,他没有期待,只想知道是谁给她底气,一而再再而三地敢算计帝王。
然而信打开后,胤禛有些意外。
明明昨夜才刚见过,信纸上扑面而来的却都是思念。
「昨夜听风,恐君凉意入体,夜半对炭火,盼君暖,如我亦,惊觉万语千言无处说」
「炭火千疮百孔,如千百冤枉,尽付窗外,化作盼雪意,蒲柳情丝应如雪,叫天地知,念呀念成了疾」
「爷,你想听雪的声音吗?」
这狗屁不通的酸话叫胤禛看得眼睛疼,眸光却被最后一句话惊得剧烈波动一瞬。
钦天监禀报上来,这几日都没有雪。
但他刚在胸膛升腾起的暴戾,凶狠,却好像被轻飘飘的雪花压住,包裹,不由自主地消散。
良久,形状姣好的薄唇轻轻呵出无声的笑,落雪的冷意从心窝子往上去,蔓在了眸底。
不用查,他也可以确定,昨晚的事儿跟耿舒宁脱不开干系。
她是个会玩弄人心的,却不是他教出来的。
那是谁,教她学会这样狡诈又勾人?
苏培盛从殿外进来,轻声禀报:“万岁爷,赵松问过陈嬷嬷和巧荷了,耿佳福晋替姑娘相中了一门亲事,是做填房……”
他期期艾艾将那人的身份说了,声音更轻,“姑娘这阵子心里不痛快,天天在慈宁宫膳房后头……玩儿泥巴,只有陈嬷嬷伺候着,倒是没跟谁联系。”
胤禛冷笑,“若朕没记错,陈医女是陈嬷嬷的侄女,还是潜邸时候朕帮着送进宫的吧?”
他记性向来很好,掌控欲又强,事无巨细都在他脑子里。
既然能瞒得住,那陈嬷嬷怕是换了主子,她的手段确实叫他有些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