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小说网>顾小碗乱世种田日常全文免费阅读 > 第134章(第1页)
第134章(第1页)
>
担心肯定是担心的,但是好像现在责备更多一些。不过这责备不是怪她不小心引发了山火,而是怪她惹事后,选择了逃脱,半点的担当都没有。
此刻见何穗穗问起,忍不住叹了口气:“现在担心又有什么用?一切看她的造化了,若是命大活下来,那是她的福气,若是不小心出了意外,仍旧是她自己选择的。”
说到这里,她的口气变得严肃认真了不少,“以后不管你们遇到什么问题,我希望你们不是像她这样处理,选择一味的逃避,这样的话,一辈子都是成不了气候的。遇着问题还是先得直面正视问题才是,若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但你们还有家人。”
几人应着声,是将她这话听了进去的,心想不管遇着什么问题,都要解决,而不是去避开,若是自己解决不了,还有家里人,难道一群人还想不出一个办法么?
也是这般,许多年以后,那何穗穗嫁了人,做了他人妇,在夫家受到不公允的待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忍让,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后有家人。
这个家里,嫁出去的女儿不是泼出去的水。
几人又说了些闲话,顾小碗最惦记的就是自己去年在山上得到的那老山参,阿拾说这种老山参,在山上的地里,时间越久就越是值钱。
可是离开了泥土,时间越久就越是便宜。
上次倒是带着去了,却没有个好价格,现在她就盼着这树种好后,出去置办农具采买的时候,能给出手了。
不然再放下去,只怕真要落价了。
翌日,天空仍旧是灰沉沉的,远处的山峦尽数被藏在了那浓郁的雾色之中,只能勉强看到一个虚影。
绣花针一般的细雨密密斜斜地洒下来,均匀地落在每个角落,何麦香起了个大早,将兔子驱赶到了原来喂猪的猪圈里,正在用钉耙扒拉兔窝里那厚厚的一层粪。
众所皆知兔子的尿也一样的臭,偏偏那两只老母鸡还来回地在边上瞧,偶尔还垂头往里啄一啄,似在里头翻找食物一般。
顾小碗看了两眼,决定不吃这两只老母鸡了,正好它们的年岁也大了。
“怎想着耙粪了?”顾小碗心想,距离地里下种子还早着,她早就将粪耙出来作甚?
这时候却见周苗头包着一块灰蓝色的头巾,背着一个背篓,里头竟是些从村北那头背回来的草木灰。
只见她往那些兔子粪上一倒,何麦香就开始将这草木灰和兔子粪均匀地扳在了一起。一面回着顾小碗的话,“我想着不是要种果树么?又是在这山坡下,也不算太远,正好这兔圈里的粪太多,我也是要给它们清理的。”
本来是打算直接将这兔子粪挑过去,但是兔子尿太多,又有些没吃完的草腐烂在一起,箩筐肯定是汤汤水水地撒,一路上臭不说,精华都没了。
所以周苗才想着去背草木灰回来拌一拌,这样干了些,再用筐挑过去的话,就好使多了。
顾小碗听到这话,盯着她俩看了片刻,很是不理解:“为何要去北边背草木灰?直接用粪桶把这粪挑过去难道不一样么?”
这话当场就将两人说蒙了,一脸呆若木鸡地看着她,片刻后反应过来,只忙不迭地拍手跺脚后悔,“完了,咱俩莫不是糊涂了,怎就没想着用粪桶来着?”
顾小碗见此,忍不住嘴角抽搐,“他们没告诉你们么?”
“这一早起来各忙各的,我们这没顾得上问,他们也没顾得上想。”何麦香直叹气,不过又庆幸:“好在没多少,一会儿我和阿苗姐再辛苦几回呗。”
顾小碗觉得着简直是没事找事,最后也没叫她俩背,而是喊了元宝来驮过去。
于是两人又反应过来,为什么要自己背草木灰,而不是叫元宝驮呢?
也好在不算多,元宝驮了两回就送过去了,只不过元宝今儿注定是不得闲了,不知道多少小树苗还等着它来回运送呢!
到底是没吃奶,胡杨虽健康成长了,但是个头小小的,小不点一样跟在何望祖和元宝的身后,有时候那路边枯草稍微茂盛些,甚至是见不到他那跟抹布一样的毛色。
不过阿拾说,那叫玳瑁色,不是抹布色。
到了下午些,上空的云层逐渐被吹开了,细雨没了,只是还带着些寒凛的风吹得脸颊刺疼,阿拾苏玉春跟何荆元父子挖树,毕竟这是要大力气的。
所以男人们去办。
何望祖还兼职跟元宝送树苗,不过走了两趟后,他就撒手不管了,任由元宝自己走过去。
元宝呢,本来就聪明,还有胡杨一起作伴,果然自己运送树苗,从何望祖他们那边装好了两筐,便准确无误地送到顾小碗她们这边来。
叫众人夸赞不已。
一天下来,除了吃饭的时间,大家没做多余的耽搁,不但将村里嫁接的小果树苗都种得差不多了,还种了不少金银花。
所以下午,阿拾他们便进了没有被烧的山里去挖树苗,管它是桦树杉树松树还是榛子毛栗等小灌木,反正一并都给挖了过来。
这山里挖树苗倒是快,尤其是那些桦树苗,好似去年撒下去的菜苗一般,如今长得齐刷刷的,一锄头下去,能挖到四五根长得板正的桦树苗,大抵半米多高,精神得很。
这些树苗好挖,也容易种活,尤其是这山里的泥土湿润不说,又才被大火烧过,下面就是旧年的枯枝腐叶,肥沃得很,刨个小坑埋了根须,再踩上两脚叫泥土紧实些,成活率不敢说百分百,但是百分之九十是有的。
便是这般,树苗逐渐往山上种植,这运送便也有些跟不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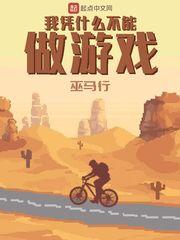

![营业悖论[娱乐圈]](/img/3715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