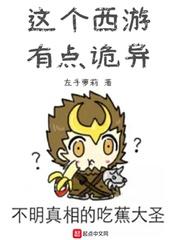456小说网>顾小碗乱世种田日常全文免费阅读 > 第381章(第1页)
第381章(第1页)
>
这些话,让孟先生那刚浮起的不安瞬间就散了,他还以为顾小碗会逼着自己现在就娶了何麦香?谁知道她只是为何麦香来管自己要一个承诺的。心中不免是忍不住一阵冷笑,暗咐道自己此前还觉得她聪慧,但到底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罢了,能有个什么见识?
只是他心中如此想,嘴上却不是这样说,且语气十分诚恳,甚至还张口就叫起顾小碗小姨,“小姨您放心,我孟言殊绝对不会负了何麦香,今日便可对天起誓,若是有半分假,我孟言殊不得好死!”
这样的誓言,如果是何麦香听到的话,只怕早就感动得一塌糊涂了,甚至不会让他说完后面那遭报应的话。
但是顾小碗毕竟是个旁观者,她感受不到这份感动,反而觉得男人哄骗小姑娘的成本真低,红唇白齿上下一碰,几个字就把人一辈子给骗得彻彻底底的。
顾小碗没有接他这誓言,而是如同这个年纪所有的少女一般,用天真疑惑的语气问着他:“不过,有一事我不是很明白,奎头他们还小,为什么会想着上战场去?”舍身为国,还轮不到这些孩子呢!
她的语气让孟先生忘记了顾小碗是顾家管事的人,又或许这几年来,她大部份时候都在依靠阿拾,所以孟先生并不清楚顾小碗原本是个什么样的秉性,如今已经完全将她当做与何麦香一样容易哄的小姑娘来看待了。
自然是没有半点的隐瞒,甚至那语气间还颇有些得意,“说起来,你怕是不信的,我只是想试一试,我究竟有没有那个本事罢了,所以在授课的时候,会与他们说些我自认为有用的道理,他们愿意听,更是听进了心里去,可见是我成功了。”他越说越有些兴奋,“我想,既然他们都能听进去,那有朝一日我与将军站在那校场里,自然也能劝动这千千万万的将士们,只要他们愿意全力以赴,那么我们的军队将所向披靡。”
这个社会的体系,让大部份男人在女人的面前,总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优越感和骄傲,孟先生无疑是这大部份中的一员,他此刻激动又兴奋,甚至没有给顾小碗开口的机会,继续说道:“你一定不知道,其实什么战术布阵,都不算什么?那战场上最重要的是勇气!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往前冲,那这强大的气势,就足已经让对方丢盔弃甲了。”
也许他说的对,战场上勇气也很重要,但是顾小碗听到他那样随意地说着,只是拿这些孩子试一试,可这些孩子却是活生生的人。
“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拿他们这些孩子去试呢?如果没能拦住他们,他们真去了战场,只有死路一条,你这不是草菅人命么?”顾小碗极力压制心中的熊熊怒火。
孟先生笑起来,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道:“这有什么?这一次凤阳的天灾,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都问心无愧!何况,我也没有直接让他们去战场,那都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死了又与我何干呢?”
他说到这里,也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忽然那笑逐渐消减下去,叹起气来,“试想我孟言殊,寒窗苦读十几年,只盼着一朝成名,却不想这好不容走到了最后一步,却叫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家子弟给捷足先登了。你说,我如何能甘心?”他是恨的,情绪也逐渐上来了,竟是与顾小碗说起推心置腹的话来。
“我好不容易投到南平王门下,却发现他不过是个胸无大志的庸碌之辈,完全无半点抱负,可是除了他,我投路无门,这些年只能跟随着他们,就是想等个机会,现在他终于愿意出去了,只是没想到竟然只是做一个铸造师!你知道我多气恼么?明明他出生贵胄,乃尊贵的皇室血脉,只要他肯振臂高呼一声,不知多少前朝遗老愿意来为他效忠,现成的江山和王座都是他的了,可他却要去为一个卑贱的草莽做仆。”
孟先生自顾地说着,丝毫没有发现自己这些话,已经超出了正常交流的范围。
但顾小碗一点都不意外,阿拾教她教得这么辛苦,她便是不能为人看病,但是用毒之上,她觉得自己颇有天赋。
所以现在孟先生这样敞开心扉地将腹中的话说出来,也是她预料中的,毕竟那午饭,可不是给他白吃的。
而在他说出这帮小子死了又何干的时候?顾小碗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孟先生真的不能离开这座大山。
这个想法,虽说是昨儿晚上和阿拾说的时候就有的,但到底还未下定决心。
“所以你是怎么打算的?”她继续问。
“怎么打算的?他自己不争气,难道还能阻止我向上爬么?这么多年跟着他,已经浪费了我多少光阴?何况那青龙军的常玉山,不过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草莽罢了。所以等我站稳了脚跟,自有我名震天下的那一日!”他从刚才的悲愤逐渐变得张狂起来,好似自己已经居高临下,睥睨苍生了一般。
顾小碗继续问,“那你还会娶麦香么?”现在他的状态,已经到了毒素侵入大脑的中期,自己问什么,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娶她?她凭什么能嫁给我?一个三言两语就能随便哄得上男人床的傻子,谁知道是不是也被其他男人睡过?”现在的孟先生,语气如同他虚浮的脚步一样,飘忽忽的,但是他自己完全察觉不到。
顾小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身来的,她将侧边那扇用于方便往下递拿粮食的侧门开了。
门外面没有任何台阶,三四米下,就是凹凸不平的山洞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