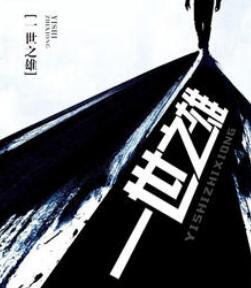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顾小碗乱世种田日常番外 > 第307章(第1页)
第307章(第1页)
>
顾四厢嘿嘿一笑,面对顾小碗的话,她并不气恼,反而笑起来:“你是不知道你四姐夫,他就是个老牛,得我在背后一直鞭策他才能有上进心。”
这说话间,何穗穗端着空相的药路过,有些不满,“娘,要鼓励人也不是用你这样先打压人的法子,那是爹性子好,若是性子不好的男人,哪个能愿意天天听自家人说自己这不好那不好。”
顾小碗十分赞成这话,连忙附和道:“咱穗穗说的很是,多夸人总是好的。”
顾四厢却是不以为然,甚至有些不屑,“那他尾巴还不得翘天上去了?”又说顾小碗和何穗穗都是没成婚的小姑娘,哪里懂得这些个道理。
闲话间,院子里新建的棚子也好了,吃过了午饭,何荆元这些个男人,披着蓑衣便赶着牛去地里,阿拾也应约去了方几田家分狼皮。
顾小碗也带着侄女们坐在棚子下拍谷穗上的谷粒。
大抵是他们才走没多会儿,就有人来借牛,只不过到底是晚了,何荆元几人已经牵着去了地里。
那人竟然有些不高兴,“我今儿好不容易得闲,还想着赶你们家牛用一用呢!你们也真是的,牛是你们自己的,哪天用不好,非得要今天也犁地?”然后一脸不悦地走了。
全程他是一点没给顾小碗几人说话的机会。
等着人走了,何麦香才气得跳起来,“这倒是有理了,听他那口气,他来借咱家的牛,还算是看得起咱家?”
顾小碗心中也是有些恼火的,尤其是这人上次来借牛去用了一天,却是一顿粮食没喂就算了,连水都是回来后,何望祖牵去溪边喝的。
也亏得这牛是有四个胃的,还能将昨日贮存在其他胃里的翻出来噘嚼。
不单是白白饿了一天不说,还马不停歇地给他们家犁了一天的地,越想顾小碗就越是生气,索性朝着棚子下的女人们都说道:“往后不管谁要借牲口,你们都不要开口允诺。”
说到这里的时候,尤其朝几个姐姐强调:“你们年纪大了,脸皮子薄,又觉得是乡里乡亲不好拒绝,既然是这样,这个恶人我来做,往后他们说什么,你们就叫找我便是,左右都晓得,这个家里是我在管着。”
顾宝云和顾三草都应着,毕竟这话就是顾小碗专门对她俩说的。
至于顾四厢,她的便宜也不好占。
这正说着,外头又传来敲门声,荣儿跑去开了,只见朱长福提着酒壶进来,随后一串没脱粒的玉米粒扔到顾小碗她们干燥的棚子下,“去给我打两斤酒来,要高粱的。”
且不说他拿玉米来换高粱酒,就是他那一串玉米,脱粒下来,怕也不过是两三斤罢了。
就这么一点,他还想要两斤酒。而且口气那样的理所应当,让顾小碗很困惑,这一阵子她忙,没顾得上管家里,是不是让大家产生了顾家好欺负的错觉?
但是让顾小碗震惊的是,她二姐竟然已经条件反射要起身去打酒了,很显然这段时间,这帮人就是叫她两个老太太给惯出来的。
所以她将眼睛往顾宝云身上一瞪,顾宝云才像是想起什么,默默地坐回小板凳上,继续拍谷粒。
继而她才朝那站在棚子下躲雨的朱长福看去,“两斤高粱酒,好啊,十斤高粱来换。”
“凭什么?”朱长福语调一下就提高了,他当然不答应,甚至马上就叫起来,“你家酿了那么多酒,自己能喝得了多少?再说一个村子里的,你有脸管我要这么多高粱?我要有这高粱我能来你家里低声下气做小伏低?”
“喝得完喝不完,倒也不要叫你来操心,反正往后就这个价,爱喝不喝。”顾小碗头都懒得抬了。
至于朱长福口中的做小伏低,或是低声下气,顾小碗是没有看到。
可朱长福大抵是因为近来顾小碗没发脾气,只当顾小碗也和她二姐三姐一样,也是见着一屋子老小都是女人,根本没有将她们当一回事,自己就要去,“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酒坛子放在哪里。”
说罢,竟然就自己要去。
他这和抢有什么区别?何穗穗周苗等人的反应,都是起身拦着他。
只有顾小碗直接握着手里打谷子的棍子,往他肩膀上就敲下去。
棍子一落,几个要去拦他的侄女都忙躲开了,那朱长福结结实实挨了打,竟然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反正当场是疼得他手里的酒坛子都落地上打碎了。
直至好一会儿,他才像是忽然反应过来,回头睚眦欲裂地瞪着顾小碗:“小贱人,你敢打……”
不过这个人字还没说出口,顾小碗一棍子就打下去,这次瞄准他的下巴打的,力道也掌握得刚好,对方的下巴当场就脱臼了,难听恶毒的话也是说不出来了,只有止不住的口水从嘴角斜流。
顾宝云等人都傻了眼,这会儿见着朱长福颤抖着身子歪着嘴站那,生怕他下一刻死了。
慌得不行。
好在这时候顾小碗终于放下了棍子,“嘴巴不会说话就不会要说了。”然后一脚踹朝朱长福,直接叫那疼得浑身发颤没站稳的朱长福就这样倒在酒坛子的碎瓷片上。
顾小碗也不管他呜呜泱泱叫,只同惊呆了的顾四厢说,“四姐,你去他家,看看他家招娣在不在,就说他爹提着一串玉米来换两斤高粱酒,咱不愿意,他自己打算去自个儿舀酒,走得一着急,在咱院里摔了。”
反正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她家院子里都是铺了光滑石板的,摔了多正常。
顾四厢猛地就反应过来了,马上起身,连蓑衣都顾不上披,“我知道了,等出了这个门,逢人我就问见着朱招娣和朱金贵没,他们家老爹摔在院子里了,脸都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