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小说网>顾小碗乱世种田日常在线阅读 > 第295章(第1页)
第295章(第1页)
>
于是她也默默地将这单子塞了回去。
韩婶子见了,心中疑惑,也一并起身,“怎了?”一面问着顾小碗,“是哪里不满意么?”
她自己也瞥了一眼礼单,想来是识字的,瞬间笑道:“别怕,这世道银子不当银子,不值钱的,还不如一箩粮食呢!”然后将单子塞了顾小碗手里,“他们家什么都是能置办的,到时候你们将穗穗风光迎过去就是了。”
又一头絮絮叨叨说,世道要是好起来该多好。
于是乎,礼单这会儿又到了顾小碗手里,顾小碗却是觉得沉甸甸的,转而往她四姐怀里塞,“你们自己看。”她是拿不了主意了,心里只想着,这要如何陪嫁才好呢?
偏这时候圣元只当他们收了聘礼单子,平日里薄脸皮,动不动就红了耳根的他,竟然是马上就喊起岳父岳母来,恭恭敬敬就行大礼。
顾四厢夫妻两个就这样云里雾里,真同他们东门家做了亲家。
后来也不知怎样说的,韩婶子说今儿是好日子,择日不如撞日,聘礼今儿就下,于是乎那圣元便急匆匆回去,不多会儿就招呼着他师弟和师妹一起来了,另外还有些相熟的小伙伴挑着旁的。
其中最醒目的,不过与一对大雁,但并不是活的,而是银的,一个小子抱着都吃力,上头还捆扎着红绸花,显然他们家一早就做好了准备的。
而这一对大雁,分别是六十多斤,纯银的,加起来正是聘礼单上的两千两白银,外用油漆刷了一层,如果不是苏氏悄悄说,顾小碗压根就没意识到,还好奇这下聘有人拿铁的大雁雕像来。
而当下一斤是十六两,所以这两千两银子如今变成了两个大雁,看着倒也不多。
礼单收了,其他的房产地契的,真不真假不假也不要紧了,反正这银子是实打实的。
所以忙活了一日,连带着婚期都定下了的顾四厢发愁得要命,嘴上当晚就起了炮,担忧不已,“这要如何是好?他们家来了这许多聘礼,先前准备的那些,倒是显得单薄寒酸了。”
顾小碗白日里已是担心过了,但是木已成舟,他们家就是来了这么多聘,人家虽说不要嫁妆,人过去便是,可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眼下见四姐夫妻两个都唉声叹气的,尤其是她四姐,早前怕人家来不了聘礼,怕女儿嫁过去吃苦,现在人家聘礼太多,她仍旧要焦虑。便道:“也罢了,那韩婶子不也说这世道粮食最金贵么?要这样说来,咱们就厚着脸皮做大户,别的没有,粮食咱家还没有么?”
不说眼下这家里地窖和仓房里的,就是半山腰那砌死了的砖窑里,也全是好谷子啊。
听得她的话,顾四厢半信半疑,“这样当真能行?”
“哪里不得行?人生在世,说白了就是为了这吃喝两个字,有了吃有了喝,还要那银子作甚?就这样算了,咱多陪嫁些粮食过去。”她当下就拍案决定。
何荆元直愣愣的,还在和顾小碗白日里一般疑惑,“打铁真这样赚钱?”
“赚不赚咱也不知道,只是这大雁铁定是他们家自己融的,有模有样,可见手艺是很好的。”顾小碗现在倒是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尤其是她这会儿想起这后搬迁来村里的人家,似乎家里几乎都有类似这样的摆件。
当时以为是他们村子里的风俗,如今她倒是晓得了,只怕都全是银子,这一帮人,也不是什么寻常的老百姓了。
正儿八经的老百姓家里,可攒不出这许多银子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是有手艺在身上的,早前显然也是在外做生意的,其实有点银钱,倒也正常。
而且眼下相处了这么久,大家衣食住行和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个区别?又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这样想通了,她也就不纠结,自去看空相。
阿拾真是在鲁石匠家里住下了,说了小外孙子有了好转,他不放心,仍旧是守在那里,等稳定了再回来。
顾小碗虽没有去看,但大概也知道如何凶险了,放在她前世那个时代,这个小外孙子怕是要放保温箱里才对。
于是也没让人催阿拾,空相这里也帮他照顾好好的。
她进了屋子,难得发现空相竟然没躺着,而是坐在床头上,手里拨着那已经盘得发光发亮的手持,见了顾小碗抬眼望过来:“我这里好着,你去歇着吧,不必总我这里跑。”
顾小碗直径走到床边的木桌上,提起水壶晃了晃,“哪里好着了?水都没得了,我去与您添来。”
待她打水回来,便挑起灯芯,准备拿剪刀去剪,空相见此,忙将他拦住:“别,就这样,本来我也不挑花绣朵,就浪费灯油,你剪了灯芯,那油就更不经用了。”
顾小碗没听他的,喀嚓一下一剪刀将灯芯剪去,又拨了拨:“咱家不缺这点,何况这些日子,村里人家时常来换酒,各样的油又得了许多,放着反而叫老鼠惦记着呢,倒不如给用了。”该想法子弄两只猫来,不然那些耗子也太猖獗了,偷吃就偷吃罢,还要将耗子屎留在粮食里,这点就叫人心烦厌恶了。
而来换酒的人多,她也起了心思,今年收来的新高粱,赶在穗穗婚期前,酿一回。
一面坐到床边,拿了自己的细麻手套继续织,一面同空相说闲话。
空相与她说着说着,不知是想起了什么,竟然是忽然红了眼圈哽咽起来,“我年轻时候这手里不知沾了多少血,现在这样的福气是不敢想的,你们都拿我做长辈来孝顺着,可惜我又没有什么给你们的,如今只觉得一万个对不住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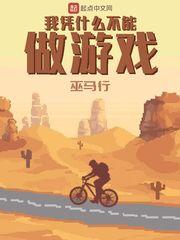

![营业悖论[娱乐圈]](/img/3715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