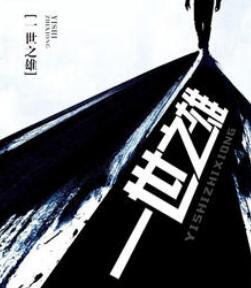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固金瓯科举最新章节 > 第148章(第1页)
第148章(第1页)
>
谢壑闻言看去?,但?见谢徽已经夺过玉佩,胡乱塞进了袖袋里?,可他还是看清楚了,因为几乎一模一样的玉佩他也?有一枚。
那?形制太特殊了,谢壑还以为全天下只?有这么一枚,玉佩整体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鱼龙,胖胖的,首尾勾衔在一处,鱼尾写了一个篆体的“林”字,在“林”字的末尾有个几不可察的小点儿,这是特制的意思,专门用来防伪的。
谢宣挠了挠头,终于记起来了,他扭头问道:“爹爹也?有枚一模一样的玉佩,我拜师的时候,还曾佩过呢。”
“您与汴京林家有旧?”谢壑斟酌着问道。
“没?有!那?枚玉佩是我自?己雕刻着玩的!”谢徽矢口否认道,毫不犹豫。
“想来也?是,我的外家覆亡多年,也?不大有什么故旧在汴京。”谢壑苦笑一声说道。
“你是卿仪的儿子?”谢徽蓦然抬头问道。
“嗯。”谢壑承认了。
谢徽目光闪烁,手指死死攥住木圈椅的扶手,他敛着眉眼,并不叫人看清眸中的神色,沉默半晌后,他深深叹了一口气,低声问道:“谢靡为何要如?此对你?”
谢壑悲凉的笑了一下,喃喃道:“我也?想知道。”
“你母亲她……”他想问一问她还好吗?如?今看来,大抵是不好了。
“在我出生的时候,难产去?世?了。”谢壑道。
谢宣蓦然抬头,他小小的心脏骤然被蛰了一下,心中暗道:原来爹爹一出生就没?了娘亲。他想象不出没?有娘亲的日子该怎么过?有多难过!
“我是被临安侯的侧室养大的,她生前是我娘的侍女,待我也?算尽心。”谢壑又道。
谢宣又被噎了一口大瓜,骇得说不出话来。
谢徽的拳头攥的紧紧的,显然出离愤怒了,平息了良久,他才开?口说道:“我之前说的话并无半句虚言,与你娘……也?……也?算不上相熟,我只?是众多爱慕她的人之中的一个,并不起眼。”
“您不必妄自?菲薄,敢揍临安侯又能揍得到的,您还是独一份。”谢壑补充道。
谢徽:“……”他看谢靡不顺眼,大抵是因为嫉妒吧。
“家里?先前的情况,你伯父都?跟你说了吧?”谢徽问道。
“嗯。”
“寒门小户又怎么可能攀附林家那?样的高门呢?!我时常站在汴京城林家店铺房檐下仰望帝阙,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你的母亲,她跟别?的大家闺秀都?不一样,不嫌弃我身上的穷酸味,亦不会驱赶我离开?,我年少的时候,时常在玉器店做帮工,你手上那?块玉佩是我刻的,不过不是什么定情之物,你母亲来玉器行定做了两?块,一个刻着林字,一个刻着谢字,谢靡的谢。只?是谢靡那?块儿被他嫌弃的扔掉了,你母亲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不小心遗落在哪一处了。”谢徽缓缓道出当年的旧事。
“本来林大小姐的定制也?轮不到我这个学徒小工来做,只?是当时我犯了错,失手打碎了客人定做的玉瓯,被玉器行的掌柜吊起来打,还要赔一大笔银子,我吓坏了,即便不吃不喝昼夜做工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银钱来赔偿,大概是我运气好,遇上了你的母亲,她心善将活计交给了我去?做,那?是块极上乘的玉料,林大小姐给的酬劳也?十分?丰厚,解了我的窘困,如?此我们算是相识了。”
“我不做工的时候,喜欢去?林家店铺下仰望帝阙,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出人头地?,出入庙堂。”
谢徽至今还能回忆起那?人的一颦一笑,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谢徽。”
“哪个徽字?是‘仰福帝徽,俯齐庶生’的徽吗?”少女俏生生的问道。
谢徽臊红了脸,军户起名?哪有那?么多讲究,但?他还是屏息道:“大抵是吧。”后来他悄悄问村里?的秀才,这句话的意思以及那?个徽字该怎么写,他自?己闲暇的时候,亦一笔一划的练习,笔画真多,写起来可真费劲啊,但?……她认为是这个徽那?就是这个徽吧。
他从未想过与她有什么交集,偶尔能抬头望她一两?眼便也?足够了。他对谢靡的不忿大抵是他认为瑰宝似的女子,并不被谢靡珍惜。
“那?只?玉瓯真的是您失手打翻的吗?”谢壑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我不认为会仰望帝阙的人,能够甘心平庸。”
谢徽出身微末,壮年封公也?能体现出一二来。
谢徽听到谢壑的灵魂一问后,沉默住了,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这样,亵裤都?能给扒干净了。
这次连早慧的谢宣都?能听懂些了,他揪了揪他爹的衣袖道:“好好听故事,不要插话。”
谢壑:“……”
谢徽:“……”
“前尘不论,自?从卿仪嫁去?临安,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谢徽道。
“临安侯与您之间……”
“以前只?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直到我从南边死里?逃生回到汴京受赏,他都?不知道有我这号人的存在。”谢徽说道。
谢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亦坦言了自?己的情况。
“我以前行七,自?幼在临安长大,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时常回家,我们彻底闹翻是因为他将世?子之位传给了谢瑞,气死了我的养母。后来,府中有人给我递了一杯添了料的酒,我和宣儿的阿娘有了夫妻之实,府里?以此作筏子,用淫辱母婢的罪名?将我逐出府去?,在家谱上除了名?,后来我带着宣儿母子去?熙州过活遇到了伯父伯母,之后的事情您都?知道了。”谢壑言简意赅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