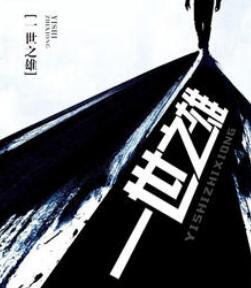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姜音祁靳西最新章节内容 > 第347章 天生要做权谋家(第2页)
第347章 天生要做权谋家(第2页)
王燕禾女士耐心说:“你外婆几天前昏迷,躺在医院,做了脑梗手术,还是没醒,都在等她醒来。”
听完,姜音看着学院封闭走道的往来同学,有人热情用法语同她打招呼,她没听见,举着手机,整个人痴痴愣愣像被抽掉灵魂。
不知道怎么离开学院,耐心听王燕禾女士说明情况。
“医生怎么说。”
王燕禾女士声音都哽咽了好多:“他们建议等。”
答案不明确。
完全顾不得一切,匆忙请假,买机票。
远在隔壁西雅图的男人,她没打招呼。
一个人落地东市的附属医院,轻轻推开23楼病房的门,里面有王舅舅和王燕禾女士。
躺在洁白床上的慈祥老太太闭着眼睛,脑部和手背皆是她看不懂的仪器同针管。
舅舅拉椅子,陪她坐下:“就不该告诉你,就知道你会跑回来,学分怎么办?”
她看着病床上的人:“外婆重要。”
“不是说想今年毕业?”
掖好被子,姜音摇了摇头:“没事,课程我自己补。”
舅舅在安排:“我来守夜,你先去睡觉,白天再过来。”
她不肯,愿意今夜住医院作陪。
王燕禾女士和舅舅回家给她带饭。
深夜,空荡荡的病房只有仪器‘滴、滴’声,小姑娘拿出平板画画,默默地守。
明明过年的时候还乐呵呵,硬给她塞红包,还说‘就你没结婚,小孩堆里,你年纪最大,红包就该拿最大那个’。
没几个月,说躺就躺。
以后谁来装傻充愣倾听她那些不为人知的心底秘密。
搁在书台的手机一直亮,恍惚闪烁,来电祁靳西。
算算,距离离开芝加哥37小时。
震动一下又一下,缠住她的视线,木然沉浸。
不接,要挨骂。
这边,西雅图谈生意的祁先生一听女佣汇报后,喉头直冒邪火,眼眸似簇了团火苗,吓得拉斐尔连连后退。
失踪37小时,放学没回庄园,杳无音讯。
跨洋电话接通。
这回,少了小姑娘温温软软的‘先生’二字,特别烦躁。
祁靳西冷漠至极,质问:“总是一声不吭就躲就跑,嗯?”
小姑娘喉头哽咽:“我…我在医院。”
男人身上的戾气不减反增:“给谁伤哪儿了。”
“我外婆住院,一直没醒,已经过去九天,医院没给准确答复,生命体征有,可外婆就是不肯醒,一旦不小心…在往下就是…醒不来了。”
一句话断续说完,她已经泪流满面,哭腔一阵一阵,那样的羸弱无助,握住手机,后背颤抖着贴在墙角,无助地蹲了下来,将脸埋膝。
是在家人面前忍了好久的眼泪,这一通电话,再也控制不住。
将近两分钟的沉默,祁靳西利落合上合同,丢给拉斐尔,单手抄兜朝大门走去,温然一声:“不要哭知道吗,乖乖等我。”
说完,男人挂了电话。
后一句话并没进入姜音的耳朵里,恍恍惚惚间,随走廊尽头消失的脚步声散走干净。
她从不奢望祁靳西那副尊贵万千的姿态纡尊降贵来到医院,没想去改变那个男人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