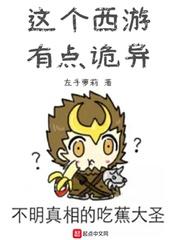456小说网>青南瓜升糖指数高吗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
“你来,将瓶颈扶正。”。
玄旸轻轻松松搞定帝徵为难的事,很快一件无可挑剔的陶瓶呈现在眼前,岱夷天生就擅长弓射与制陶。
洗干净手,玄旸坐正身子问道:“不知道徵叔找我有什么事?”
“你别跟我装糊涂,过来,陪我到外面走走。”帝微起身,手指池苑外面的河堤,桑木郁郁葱葱。
帝微一起身,服侍的仆从纷纷俯伏在地上,对他像神明一般敬重。
玄旸陪伴帝徵,两人离开池苑,跨过木桥,来到相对僻静的桑林下,帝徵的两名侍卫被留在桥对面,没让他们靠近。
“徵叔烦虑时,会到池苑小屋制陶、做木工活,说是手里有活做,心里不烦躁,再烦恼的事也能在做活时捋顺。我想我拒婚的事,不至于令徵叔烦恼。”
帝徵冷哼一声,带着愠意:“阿瑤已经与我说了,说她前日见过你。你尽找些荒唐的借口拒婚,此事稍后再谈。”
“可是为了河东诸部内迁的事?我来文邑的路上,就遇到不少从脊山道逃进来的流人,这些时日应该更多,毕竟鹞城与鸱鸺氏的战争还没停息。”玄旸站在树荫下,仰头见树上桑果累累,他随手摘下一串。
池苑外的桑林也归宫城所有,没获得允许,他人不敢采摘。
“如今鸱鸺君遭杀害,鸱鸺族众四散,鸱鸺君的弟弟鸱鸺期想率领族人内附文邑,遣人向我献宝乞求收留,他们人数众多,进入文邑如果不能妥善安置,必会生乱,我不敢允诺。鹞城士兵对鸱鸺人大肆杀戮,连孩童都不放过,做下人神皆憎的罪行,不只鸱鸺人失去家园,你也见到了,河东的部族纷纷外逃,都怕受到殃及。这么一大群人挤在脊山道上,又因为食物不足,互相攻杀,留下数十具尸骸,血染谷道。这些流人通过脊山道,进入文邑后,在南汾四处流窜,乱糟糟一片,如今连文邑都受到波及,我不能不管了。”
帝徵皱眉,他见到玄旸手中暗红的桑葚,大概是想到血液干涸后的颜色吧。
没搭理帝徵的小心思,玄旸递给他一把桑葚,不想他还真接过去,捻起一颗,放进口中。
“要是鸱鸺期能打回去,收复部分土地,河东诸族见时局平定了,会返回故土。人们总是思念故乡,何况他们流落异乡过着苦日子。”
“我可没打算派遣军队前去援助鸱鸺期,文邑的北面一直遭受靳人侵扰,南面还有好战的山楯人,眼下腾不出手去收拾鹞城。当然,如果必须出兵,我会征召国中青壮,训练他们,再叫国人赶制骨石武器,也能在六十天内装备出一支军队来。”
“这么说来,微叔是想让鹞城与鸱鸺议和吗?”
“我确实有意派遣一位使者去鹞城,向鹞君施压,劝告鹞君要么退兵,与鸱鸺议和,要么我出兵帮他们议和。”
玄旸用手指轻蹭掌心染上的桑葚汁,像似一手血般,他淡语:“我知道有一位高地旅人合适出使鹞城,他人正好在文邑。”
帝徵挑了下眉头,他道:“我也可以收留鸱鸺人,并将逃进文邑的所有河东部族聚集起来,全部安置在北积,由你来治理他们,这些人只要被管住,既能耕种农田,输送文邑粮食,又能成为镇守北地的主力。玄旸,我将授予你玉圭一件,并封你为‘北伯’。”
玄旸似乎一点也不意外,他沉默着,在思考。
“你以旅人的身份拒婚,声称无法迎娶帝女,我以前说过,只要你想夺回玄夷王位,我会助你。如今,我分封你为北伯,你还有话说吗?”
玄旸将修长的身子往桑树上一靠,穿过树叶缝隙的阳光照在他肩上,他望着树上啄食桑葚的鸟群,鸟儿叽叽喳喳,在枝头跳跃、扑翅,过了好一会儿才回道:“我无法允诺。”
一阵沉默,帝徵面有愠色。
“你与你父亲玄倬很类似,有庇护他人的能力,却不愿担起责任,将上天赋予的才能掷之地上,毫不爱惜。”
帝徵喟叹,似乎还有些愤慨的情绪在里头:“你父终其一身,自晦避世,不愿有所作为,寿命又短暂,使得名声不能彰显。我与他是至交,每每想起,都为他痛惜。”
“玄旸,你明明具备他人不具有的勇气,面对权力却又比任何人都懦弱,你到底在惧怕什么?”
“大概……”
玄旸抚摸腰间佩戴的匕首,喃喃道:“是死亡吧。”
“这是个残酷的世道,如今一个聚落,一座城在朝夕之间被毁去,留下遍地尸体,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也曾卷入战争,从战场上回来,亲手缝合伤口,修理残破的武器,在入夜时,因伤痛无法成眠,想着混战中刺伤的敌人有张稚气的脸,他也是谁家的儿子,也有人在牵挂他。徵叔,我当不了君王,或者封伯,我可不愿意为成千上百人的性命负责,我只能为我自己负责,我无法允诺。”
“恐怕,人往往得去做不情愿的事,哪能事事随心意。玄旸,人们常说上天给予的赏赐不要,会遭到上天的惩罚,你好好想想,再答复我。”
“上天惩罚这句话怎么有点耳熟。”玄旸嘴角有笑意,同样的话,他舅父舒渎君也对他说过。
“徵叔,文邑最不缺的就是人才,王族子弟中多有能力出众的人,身份尊贵能服众,又对国家忠心耿耿,可以派遣他们镇守北积。”
帝徵背着手,望向林间的鹿影,仿佛没听见,自顾念叨:“我多年前在池苑养了一头獐子,喜爱它灵巧聪慧,时常与它玩戏,一日喂饱后,忘记关上苑门,獐子毫不留念直奔向森林,再没回过头来,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