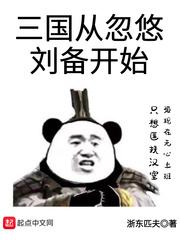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宋书晚傅三爷 > 第77章 你现在想要么如果你想我留下过夜(第2页)
第77章 你现在想要么如果你想我留下过夜(第2页)
“脑袋磕破,烧酒清洗伤口了。阿郎忘记,因为阿郎没有拉住我,我磕在花坛上的事情了?”宋书瑜眼神睇了睇傅灼走后,颖儿从酒窖取出了一小瓶女儿红,在小碗里倒了些,火折子点燃了烧起酒来,毕竟屋子里酒酿气需要说法,“阿郎看完环儿写的爹字了?”
“看完了。”
“写得好吗?”
“写得挺好的。明儿你也看看。”
“那环儿的父亲泉下有知也应该开心的了。我便不必看了吧。”宋书瑜低声说,“烧给他爹看看?”
周芸贤脸上不自然,“你是舅母,孩子会写字,如何不必看?”
宋书瑜轻笑,“好。天亮看。环儿那个短命鬼爹死的早,孩子还怪争气的,咱得给孩子找个爹才是,男孩儿得有父亲管教的。”
周芸贤皱眉半天,也不好回什么,看了看那烧过的酒碗,随即将视线落在宋书瑜额角的伤口上,青了一片,创口还出血,他伸手去碰伤口,宋书瑜嫌恶地把面颊别开了,不愿让他的手碰到她。
“还疼不疼了?”周芸贤以为她疼。
宋书瑜沉声说,“刚碰到的时候疼。那时问好些。这时不大疼了,问反而觉得没必要。”
周芸贤察觉到妻子温顺中的锋芒,“那你那时候乖一点,不要和我闹,让我先睡一觉起来,再说找狗的事情,那我也不至于和你争执。你的性子应该改一改的,这七年你的贤惠是装出来的,我见到的不是你真性情?”
“对。都是瑜瑜的错。瑜瑜不懂事。”宋书瑜嗓子软软的,“这七年的贤惠的确是收敛了心性的。毕竟我出嫁前没做过家务,也没煮过饭。嫁来你家什么都学会了的,结果换来了什么。”
“娘子,你别拒人千里之外。”周芸贤今晚很有些愧疚,“我们恢复到以前恩爱的样子。等明日本卿将臣子规交上去,过了太子那一关之后,咱们把房圆了。以后日子安稳地过。”
宋书瑜心里很疼,对他来说妻贤妾艳齐人之福,对她来说是满门待斩灭门之灾,日子怎么安稳的过,为什么他说得轻飘飘的好似很简单。
“好的。阿郎可是冷落人家太久了。七年呢。不然,瑜瑜早就做母亲了,有个小东西缠着瑜瑜叫阿娘的。”
周芸贤在脑海里构想那个画面,倒有几分向往,有了孩子,她便会将宋家的事淡忘了,出嫁以夫为天,原想等她死了扶正莲莲,这几日却越发觉得莲莲不如瑜瑜稳重有主母气度,尤其昨日他在抄臣子规,莲莲不说息事宁人,反而在书房外吵闹,他又在权衡。
“你现在想要么?如果你想,我留下过夜。还有一二个时辰天明。”周芸贤说着幽幽一叹,“你如何不早几年告诉我,你同太子之间是清白的。我们白白虚度这些年。”
宋书瑜还是那句,“我不知阿郎质疑我会婚前不检点。”
但和太子之间清白么。自然不了。除了那道线,什么没做呢。那哪里可以认为不进去就是清白的。她不至于那样想。这世道交换个手帕就不清白了,何况裤子都交换了。哎。。。
“我月信没干净,而且头破了伤口疼,找一夜狗脚底磨泡并且有点发烧了。”宋书瑜温温笑道:“想要也是有心无力了。待我养好身子,待你上交了臣子规。再。。。”
再字后面不肯说了,便那样眼睛湿漉漉地凝着周芸贤。
周芸贤被妻子注视着,竟觉得手心有几分薄汗,这感觉是在尤氏那里没有过的,和尤氏是同乡,属于发小,素来是尤氏主动,他没有被尤氏拒绝过,见惯了尤氏那个骚样,当下更觉得瑜瑜珍贵难得。
周芸贤在梳妆镜前看见了傅灼带来的餐食,又看见食盒上写着‘上京食府’字样,不由说道:“你打包的饭菜回来吃么?”
宋书瑜不知他为何问,“是。怎么?”
“上京食府的东西贵得要命。你怎么不回家自己煮些吃?这一餐少说五六两。我一个月才几个银子。你一顿饭花我三分之一月俸。这三个月俸禄还被太子停了,更该节俭。”
周芸贤不悦,责备道:“有嫁妆也不能挥霍,孩子以后事多呢,念书,仕途,成家立业,处处需要钱!现在培养小孩儿可不似我小时候放养,各门功课都得请师傅教的。”
“哪个孩子以后事多呢?”宋书瑜顿时下头。周环吗?周环以后的人生大事和她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