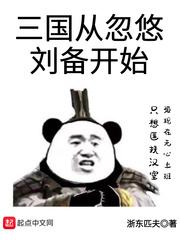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聘狸奴纳猫契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
“我都说了,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故人。”常笑继续低头翻书。
“我还是觉得不自在,我想走。”
常笑忽然牛头不对马嘴地问道:“你可知,‘玲珑骰子安红豆’下一句是什么?”
“答对了就放我回去?”
“答对了我去把盯着你看的人揍一顿。”
“这不太好吧。”
常笑叹了口气,合上书道:“我带你见一个人吧。”
二人驻足在一间名叫“云山庙”的院落里,周遭被茂盛树荫遮蔽,斑驳树影,飒飒微风,俨然不同于雾海七星屿,六角攒尖顶的石亭,靠墙挺立的修竹,看上去是个纳凉的好去处。
周遭却寂寥无人,吹着惬意的风,岑松月扫视庭院,问道:“你莫不是诓我,哪里有人?”
常笑道:“庙中庙,你可曾见过?”说罢抬脚迈上石阶。
岑松月跟进去一看,却与普通庙宇别无二致。待他详细观之,才发现供桌上摆的竟是一盘红烧鲫鱼,两旁燃烧的烛火呈幽蓝色。供桌后挂了一副貍奴戏春图,画面中,貍奴身着华丽外衣,站立似人,柳树儿下放纸鸢,绿茵地上三两个扑蝶儿,花外楼宇上,一只猫儿懒倚美人靠,手中摇扇,一副娇滴滴可人儿样。
岑松月心下道:奇也怪哉!竟有庙宇专供貍奴子?正想开口问话,却被常笑拉住手,随即一跃,再睁眼时周遭已经暗换芳华,只见此地与方才见到的图画别无二致。辛夷花树倚楼舒展,花开满楼。柳静风停,放纸鸢的人驻足而望。常笑向楼上招手道:“小芙娘,快下来!”
忽听得“嘻嘻”两声稚嫩的笑,楼宇上传来一阵踢踏下楼的轻微响动,那人一路跑一路喊:“爹爹!”
岑松月惊道:原来他都当爹啦!此时心中不免落寞,自己无端地成了孤魂野鬼,还眷恋人间做什么?做个没人管的孤魂野鬼倒也不赖,自此休要说什么七情六欲,三魂六魄。思及此,只听见一声“娘亲”,这小姑娘的声音甜上心头,岑松月心道:要是我能有个女儿该多好?随即应了声,只一瞬,那耳朵根子都红透了·····
常笑低头看他,解颐道:“她乱喊没事,她才五岁。你乱答应可不行,你也才五岁?”
岑松月只觉一双耳要烫化了,连忙抬袖挡脸,心下痛骂自己:真是令人······喷饭!
哪晓得常笑是个人来疯,捉住他袖子不许他挡。岑松月连连价叫苦:“恩公快快忘了刚才的事儿吧!”
“我没关系,你问她答不答应?”常笑抱住女儿凑近了些,给常芙使了个眼色。常芙是个小粘人精,身子一歪就倒在岑松月身上。
岑松月自知是玩笑话,顺手抱过常芙,也不重,颠了颠坏笑着溜开道:“我们不要你爹爹咯。”幼女笑声清脆,引来旁人羡煞的目光。
这厢一路徐徐走,一路慢慢看,岑松月做个新客,只觉得这里是画中仙境,相忘于尘寰:柳叶儿逐风摇曳,迎春花瓣饱蘸春色,抱在树杈上,落英也不减芳华。常笑捏指吹哨,唤出一帮花斑黄毛的虎舅轿夫,抬着一顶饰了流苏的大轿,岑松月一瞧之下惊出冷汗,但见他们形似人站立却长有兽首,个个都赛那林中王,人见了生畏,汗毛都倒立起来!常芙却是不怕,小孩子心性就想着玩儿,三两下蹦跳着抢进轿中。
正当岑松月出神之际,常笑凑在他耳边道:“随我去吧?”
岑松月迟疑道:“你家?”
“嗯。”
“嗯······那便叨扰了。”
轿内是一个温馨的所在,常芙坐在常笑腿上,眯眼犯困,岑松月也有些困倦,别看他坐得端正,心思却已经歪到梦境······朦胧中听到几声呵斥:“慢一点!轻点儿!”听得不太真切,倾身便睁眼。
“不舒服吗?”
岑松月惺忪着眼,翻了个身,打算续眠,手极不安分地放在“枕边”,摩挲了两下做个瞌睡虫。
常芙小女枕着常笑另一条腿,常笑解颐。
岑松月睡了一路,停轿的时候却忽然睁眼,像是预知了什么似的,常笑更觉有趣,猜出个七七八八,笑笑却未曾言说。
衔蝉之家坐落于辛夷花林中,粉红落英下粉墙黛瓦,出水芙蓉上水榭楼台,其侧兰草饶墙、凌霄骑瓦,鱼戏水中、如游空中。走过影壁,一方幽静池塘,残留纤细枯荷,深不见底,抬头一望,瓦檐下的石榴开得正烈,榴花如火,美艳不可方物。此间无“季节”,四季恒定,春之明、夏之烈、秋之暖、冬之寒,于众妖而言是外界的感触,猫生性畏冷故有“煨灶猫”之说,生活在这里的猫妖,自然逃过了命定的苦难。
一条巷道里藤蔓肆意疯长,漫到脚边,常笑拨藤寻径,进到一个碧岑岑的小院——芭蕉翠色、亭亭菡萏、绿池锦鲤,通通相得益彰。小池塘之上、屋舍之前,架了座充当景物的竹桥,三人跨桥而去,走进屋里,岑松月以为是个不太宽敞的逼仄所在,不曾想屋内结构颇为精巧,一条楼道往下另还有一些屋子,走在宽敞的廊上视野开阔,能眺望到远处一座塔,令人神怡。
撩开珠帘,原来已经进到常笑的房间。屋内物件齐全,东墙上挂着一幅寒梅图,画中梅树枝杈不甚明朗,点点滴滴红盖住稀稀疏疏枝,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岑松月道:“恩公喜欢梅花吗?”
常笑道:“不喜欢,只是喜欢画,又找不到什么中意的,索性只画花,画了这么多也没练好,见笑了。”
岑松月道:“我觉得画得很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