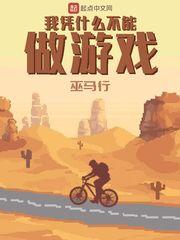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旷野上的星 > 第29章(第2页)
第29章(第2页)
宋裕睡得很安静,但是神情很不安。
和寻常被梦魇折磨的人不一样,他没有变幻扭曲神情,也没有辗转反侧。他只是流露出不安,然后便静静地凝固在那不安之中了。如同一尊被摆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棺中的雕像,在游客来来往往间,他的不安寂静成无法被凡人参透的永恒。
“嗯?”
宋裕带着重重的鼻音,嗓音略微沙哑,刺眼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令他有些睁不开眼,覆在他薄薄眼皮上的柔软睫毛被染成了金色,他慢吞吞伸了伸脖子,带着不清醒的懒倦:“我吵到你了吗?”
“没有,你很安静。”如果不是还在呼吸,简直就是一尊死物。
“那就好。”他因为久睡而沙哑的嗓音,如同刚上完松香的大提琴,低沉又性感。
楚岁安听他的声音,有种耳朵被带着薄茧的手揉搓过的感觉:“。。。。。。手剎后面有矿泉水,新的。可以随便喝点。我们快到加油站了。”
宋裕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天亮,但是人类身体构造的局限性不允许他适应如此耀眼的太阳,他眯缝着眼睛感受了片刻阳光的热,伸手把原本放倒的椅背立了起来。
他看到楚岁安所说的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等到加油站,换我来吧。开多久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楚岁安扫了一眼车上的移动电视,回答。
宋裕正在喝水,听了楚岁安的话以后动作一顿,一线水珠从他的唇缝漏出来,滑过他的下巴,滴在了他光洁的锁骨上。
楚岁安从后视镜瞥了一眼他骨骼轮廓上的光泽。
他惊愕地看向后视镜里丝毫不见疲惫的楚岁安:“你一直开吗,没休息?”
“十多个小时,还好吧,这条路基本上没有车。”楚岁安没觉得怎么样。
“。。。。。。辛苦了。”宋裕吞咽了几下唾沫,才缓解了喉咙的干涩,他似乎再一次清晰体会到楚岁安所说的‘我一个人也可以’。
其实在找信号的途中,虽然看似他拉着楚岁安避开了很多凶险,但后来在回去剧院的路上同楚岁安闲聊的时候,问她如果只有她自己,在他们遇到的各种情况里,她会怎么做。
楚岁安和他说了许多在战区碰到紧急情况的避险方法,也很详细地讲解了针对他们遇到的,如果他不在场,她又会怎么做。她说人们被未知的威胁恐吓住了,所以有些草木皆兵。要想深入拍摄这一切,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形式上彻底融入他们。
不要想什么这里是本罕利,是闭塞的,人人被洗脑的地方,要想这一切都是人,人给人建造的战场,荣誉或地狱。
她知道怎么保护她自己。她不需要任何人。
“你想回去吗?入关之前都来得及送你回去。”楚岁安冷不丁出声。
宋裕身形顿了顿,看向她,目光带着软刺:“怎么了,怕我给你添麻烦吗?”
楚岁安扫了一眼后视镜,觉得他那眼神就是在说“你敢赶走我一个试试”,只不过这个人不会咬牙切齿地说出来这么幼稚的话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