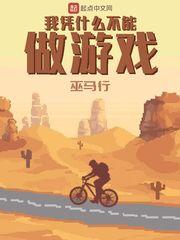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弘历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
冼安然嗫嚅道:“王福子的致命伤是头部钝器打击。胸口也有打砸的痕迹,死后泡在什么密闭是容器里,最近才把他捞出来骨肉切割分离,袋子原来装过腊肉,上面有油渍,洒了老鼠药,缺的那一根肋骨,有个细心的民警已经帮忙找到了,在一个老鼠窝里发现的,一同带回来的还有老鼠窝里的部分材料,都是沙发碎片,很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检验科查验后,很快就能知道布料的来源,依我看,不像是李盘他们几个人做得出来的。”
卫臻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表面看起来他们几个是好人,邻里风评都很好。王福子、李彪贵、李小兵都是死有余辜。但是别忘了一点,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
王北佶低头看着手机,说:“眼下的问题是……局长刚刚在工作群里发了一份报告。市法医那边刚刚有一个重大发现,被当成曾宝贤下葬到曾家祖坟的那个无名尸骨,根据年龄和身高筛查失踪人口,确认是陈校长高考失利成了疯子后走失的大儿子。死因同样是钝器击打头部,和王福子一模一样……”
卫臻愣住了,拿出手机放大报告,盯着结论陷入了沉思。
这时女侦查员的手机响了,她接通电话,一面点头一面朝三个刑警看过来。
“是不是李彪贵的老婆陈小柔回来了?”冼安然问。
女侦查员挂了电话,说:“现在陈小柔在公安局门口撒泼闹呢,带着几个亲戚,口口声声说是她儿媳妇陈文静害的她儿子李小兵。”
王北佶皱眉:“她有证据吗?在那胡闹!”
女侦查员:“她说陈文静自从嫁到他们家,一直都对他儿子不好,天天赖在床上,不给他儿子洗衣服做饭啥的,一直都是她在家做饭……现在他儿子没了,陈文静带小儿子东家躲西家藏,还跟那个麻将馆的老板眉来眼去,不回来给上学的那几个娃儿做饭洗衣服,一定是陈文静下的手。”
王北佶扔掉手里的烟,冷笑一声:“她还真是说得出口,你记得之前咱们上门访问的事吗?七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小的两个是龙凤胎。李彪贵的心脏血液与龙凤胎胎的毛发DNA检验统一,有直接亲缘关系。李彪贵和陈小柔以及李小兵一家三口,都不是啥好东西。陈小柔涉嫌虐待和胁迫发生性关系。现在,李彪贵和李小兵已死,光凭陈文静的口述,没有证据,很难定陈小柔的罪。她倒好,自己撞上来,拿着她那一套说话,陈文静她妈收了他李家的礼金,被逼着嫁到他李家,就得给他李家当牛做马,替他儿子守活寡呢?”
卫臻见王北佶义愤填膺,忙道:“王队先别生气,陈文静说的也不完全是真的。一个真正被胁迫侵犯的女人,不会像她那样,面对警察就像面对街坊邻居一样,态度和气,问什么说什么。据附近的邻居说,她平时会出门骑自行车买菜,给小孩买零食,完全有机会报警或者逃跑,她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有些事,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王北佶意味深长地看了卫臻一眼,说,“在这起事件中,李彪贵遇害不假,但真正活受罪的是陈文静。李家父子一死,陈文静畏惧的人没了,她肯定是心理上放松了,才敢回答那些话。”
卫臻冷哼:“李家父子是死了,陈小柔可还活着呢。这个女人十里八乡都说她强悍,陈文静敢对我们说实话,难道就不怕陈小柔回来找麻烦。”
王北佶疑惑地道:“是啊,陈小柔一个悍妇,老公儿子都没了,肯定要把怒火撒在陈文静身上,陈文静还敢去火车站去接陈小柔,有趣……陈文静呢,现在在哪?”
女侦查员说:“她早上去接了陈小柔后,回头就跟麻将馆的老板守在诊所陪她小儿子输液呢。”
红日西沉,晚霞漫天。卫臻手指夹着烟挠头,无精打采地瞥了一眼不面色凝重,说:“这里是没得啥看头了。走吧,去诊所瞅瞅吧,瞅瞅那个娃儿跟陈文静。”
四人的寻访到底是晚了一步,诊所的医生说,陈文静和那个孩子已经回家去了。
卫臻问医生:“那个小孩平时身体咋样?经常来医院吗?”
医生点头,说:“母子俩都有很严重的皮肤病,浑身上下起疙瘩。我们这里不敢确定究竟是啥子原因导致的,只敢给她开一些杀菌消炎的药,嘱咐她多喝水注意卫生。让她去市区大医院检查,她又不肯去。就这样一直拖,夏天一来,就经常带她孩子来这输液。”
“得,还是亲自去她家跑一趟吧。”王北佶说。
“我饿了,先吃点东西吧。”出了诊所,冼安然看着路边支起的摊位,闻着诱人的烧烤味,饥肠辘辘。
“行啊,饿着肚子也干不了事。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卫臻手一挥,大气地说。
王北佶勉强笑了笑,说:“多谢卫队,那我就不客气了。”
四人分别点了自己喜欢的素菜和荤菜,找了个座位坐下闲聊。还没聊两句,卫臻就探头看了一眼烧烤老板,低声说:“欸,这个烧烤老板跟对面的餐馆是一家吗?我刚刚让他烤茄子他说没有,要等会儿,现在又直接从餐馆里拿了几个茄子出来。”
深谙街头市民人际关系的王北佶递了一支烟过去,说:“不是一家,但是做生意的嘛,都会互相帮忙,为了迎合客人的喜好,没有也会想办法弄出来。”
卫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王北佶又递了一根烟给冼安然,冼安然摇摇头,拿着手机偷空给李盘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