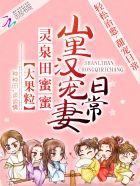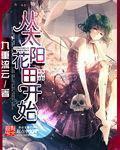456小说网>从零开始的最强之王 > 第158章 演出与演说(第3页)
第158章 演出与演说(第3页)
唱完歌,江姐和演司令员的开始对话。
他们每说一句话,大家的脚步就向谁靠近一分,不是重重的跺地声,是布鞋的沙沙声,整齐而响亮。
台下的观众经过三场的剧情才渐入佳境,明白了江姐现在的情况和背景。
他们吞咽着口水,消化着台词和歌词,与台上的人共情。
“千重苦,万重恨,莫压在心头,莫压在心头,莫压在心头……”司令员唱道。
这一幕很感人,张辰却关注起她们的衣服,打的补丁方方正正,无缝衔接,没有褶皱,干干净净,不似落难时的衣服,像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破洞装。
不出意外,化悲愤为力量的桥洞不会少,女主角接过未婚夫的遗物,成为新的双枪老太婆。
张辰一脸问号?
有些戏剧化,不过大家都歌舞真是振奋人心。
第一个歌剧高潮过了,为了后面精彩内容做铺垫,也为了防止疲劳,接下来肯定是平淡的剧情。
装死的旁白发出了声音“在江姐领导下,游击队员和当地百姓在华蓥山一带取得了多次胜利,敌人对江姐的追捕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忙完上一场大家赶紧换了一套服装,观众们是脸盲,群众演员是消耗品,这样频繁地换装会让观众有所满足,得到被重视的感觉,毕竟觉得有很多人为他们表演服务。
艺术是引人入胜,而不是引人入睡,最好爆点不断,不然很容易失去热情。
插科打诨的剧情出现了,敌人抓住了一个老头说是江队长,结果是蒋对章,蜀川话一律第三声嘛。
领导还是给面子,开怀大笑起来,边上的人附和着一起笑。
座位后排有人拿起手机转移了注意力,已经把这场歌剧当作形式的活动了。
台上的光打在主演脸上,台下灯光关闭,只有玩手机的人都脸在发光。
就像课堂上,老师说的一样,你们在下面的动作我看的一清二楚。
张辰记得以前无论学校还是村里,组织看表演都是很积极的,也很尊重演员,该笑就笑,该鼓掌就鼓掌。
有人遥首企盼却又正襟危坐,议论两句却又怕打扰别人,纯朴和纪律性十分明显。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气,哪个合适不是他决定的,是社会决定的。
老黄牛也被拉出来走了一圈,只是失去了灵性,被驯服好了一样,对着观众不断地哞哞叫,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悲伤。
因为下一场,江姐就要被叛徒出卖了关进了渣滓洞。
叛徒,江姐,快要牺牲的战友,一人一句地唱,越唱越快,形势愈来愈激烈,观众也终于认真地看了起来。
“乌云染不黑天边月,狂风吹不落满天星,梅花怒把春来报,战胜严冬百丈冰。”终于,牺牲的牺牲了,被抓的也被抓了。
痛恨着叛徒背叛革命,心纠牺牲的同志的壮烈,担心被出卖的江姐的未来。
合唱的唱腔已经完全变得悲戚,不禁让人回味之前豪情壮志,要投入革命的歌舞。
随着情节发展慢慢进入尾声,全场的景象都变成了灰暗寂寥的地牢,台上的人也不再唱歌,顶多哭唧唧几句。
就是为了最后的爆发而铺垫。
灯光一暗后一亮,重新出现的江姐等人共同拿着一块布,红色的布,这是她们编织的红旗。
张辰知道这是最后江姐牺牲后要摇晃的红旗。
就在所有人站在舞台两侧,准备迎出在投影的夕阳下走来的江姐时,发生了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