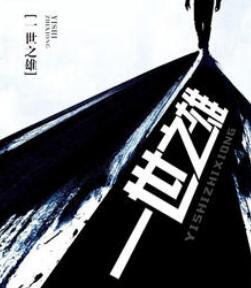456小说网>时光的印记钢琴曲简谱 > 02(第1页)
02(第1页)
在我工作生涯中,相当长的时间是任职企业的工会主席职务,许多年前工会建了一个带喝茶喝咖啡的不大不小的职工书屋,刚建成时为书屋征询名字。在大家起的许多名字中,我觉得有的叫得太正统,比如职工书屋,就无法充分表达我们在小区寸土寸金的地方建书屋的感情和希冀;有的建议叫成咖啡厅或茶秀,我觉得更不能体现提倡大家阅读的愿望。为了充分体现阅读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喜悦和收益的这一有益实践,并且提倡大家愉快地去阅读,我最后确定将书屋的名字定为“悦读书吧”。一层意思是劝学,是说让大家尽情地看书吧;一层意思是书屋的名称,指阅读的书屋。在这过程中,把自己喜欢看书的情怀融入这项公益活动中。书屋的门头也是我亲自审定的,门头的样式是一本厚厚的翻开的书页,在绿色华表柱的支撑下生机盎然地在门口迎接着大家。这个“悦读书吧”后来经常被人们简化成了“书吧”,很少有人给我讲:愉快地读书吧!这多少让我有点失落。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它被评为了全国优秀书屋,而且,大人小孩没事的时候去得还是比较多的。
从年幼时一本两本地到同学家借书看或站在街头连环画摊看连环画,到现在在设计新潮琳琅满目种类多样的各种网红书店打卡,抑或是在自己一面墙的书柜前流连,变的是阅读的环境和阅读的内容,不变的是自己内心对阅读的热爱和向往,还有阅读带给自己的愉悦感受。
房子
我和大多数出身农村的人一样,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们农村的老家有大大的院落,有大大的却很简陋的窑洞,虽然不是多么便利,但从来没有担忧过会没有地方住。在老家的窑洞里随便哪安个床拉个帘子不就可以住了吗?或者一家人干脆都挤到三四平方米的炕上,平展展的,除过偶尔的不方便其他还都好吧。再不济,像大学集体宿舍一样一人一张床还是可以的吧?或者像我的高中老师的宿舍一样,一间房前面是一张办公桌,后面是一张单人床。这是我1987年大学刚毕业时关于住房的一些粗略想法。那时我对单元房还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大学期间偶尔一次去过城里的同学家,也没有敢认真地看仔细地问。谁知道,在毕业后十余年里我为了有一套能容纳我们一家三口的房子而看尽了各色人等的脸色,直到我作为工厂的骨干人才,在1996年交了在当年算作天价的购房款后,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六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关于房子的不愉快经历才算告一段落。
大学毕业进入一个三线工厂后,给我的第一个关于房子的记忆是我们工厂的单身楼和招待所。这个位于山沟的三线工厂以前招的大学生比较少,少量的大学生进厂后都是在离沟口七八里路的沟里的单身楼住,两人一间房子。这种1968年建厂时依塬而建的单身楼共有两栋,一栋男职工楼和一栋女职工楼,另外还建了一栋一居室的母子楼。到了1987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工厂一口气招了三十多个应届大学生,可是当时却没有相应地腾出这么多的床位,需要一个一个地往以前分配的两个人的宿舍里安插。我被安插进已经有两个人住的宿舍时,就遇到了麻烦:这个宿舍里已住了几年的两个人,不愿意给我腾出放单人床的地方,我的单人床就安放不进去,我就无处睡觉。我们处长就协调我住进了设在一进山沟的沟口的工厂招待所。
我大学毕业去的这个工厂是个三线厂,1968年建在了秦岭的位于太白山西边的一个沟道里,这个沟道名字叫麦李西沟。一条沟道两面山塬相夹,中间是一条河,河两岸是高低不平的土地,河边是一条马路。招待所建在一进沟稍微宽畅的一个平台上,是四层高的楼房,但并不是现在的标准间,而是一层楼设计了集中的供应热水凉水的水房,水房两边分别建有男女卫生间,主要是为了接待来厂里办事的外地人员。办公楼建在进沟后往里走两公里左右的一块平地上,车间在更往里走的马路两边择地而建,单身楼和职工食堂都建在沟道的最里面,距离沟口七八公里。
这年7月大学刚毕业报到后,因为宿舍暂时进不去,我一个人就住在工厂招待所的四楼房间里,告别了当时的大学生活。每天上班到位于办公楼一楼的办公室给领导们师傅们打水,给办公室拖地拿报纸,熟悉工厂各类文件,下班后就去单身楼旁的职工食堂,吃过饭后再走回七八公里外的沟口招待所。每天因上班、吃饭、回招待所就要在沟里走几十里路。当时是夏季,招待所建在山塬下,也不通风,7月份的天气闷热难受,在整夜电风扇的嗡嗡声中我难以入眠。大学刚毕业的不舍之情和刚进工厂的不适交织在一起,每天深夜一齐涌向心头,眼泪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湿了枕巾,一个月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之后我的宿舍终于分好了,我加入集体之中,住上了三人一间的集体宿舍。
一年后,我结婚生子,又是两地分居。可我总不能带着孩子住集体宿舍吧?于是,我央求我们处长给我协调工厂的母子楼。可谁知因为我爱人不在这个工厂上班,我属于单身职工。当时,在这个以双职工为主的大型工厂里,单职工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我们处长借机善意地批评我找对象没有社会经验,没有经济头脑,不找本单位的,而是找了个外面单位的,说现在有了孩子,按工厂积分排队,我就没有希望可以分配上住房,顺便提到了以前给我介绍对象我没有谈的话题。但说归说,他还是积极协调,然后在单身楼给我协调出了一间房,我们母子俩就住进了单身楼四楼的一间房里,邻居也是一些结婚后不够条件分房的小两口、小三口,还有年龄大一些的双职工。这间房子解决了我和孩子住宿的燃眉之急。我当时内心还是挺满足的,毕竟我在那一拨分配进厂的学生中是先结婚生子的,能在工厂单身楼找个住处,既经济又安全方便,也算不错的。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学生结婚后都去了沟口租住民房了。即使到现在我经历了许多住房的曲折,住上了自己购买的大商品房以后,偶尔想起以前在老厂区的单间房,心里还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我和儿子住的单间房放着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一张单人床有床头,一张单人床还没有床头。年长的同事借给我一张钢丝床,支在房间内靠门的一面墙旁,轮流来帮我看娃的婆婆妈妈就睡在这张钢丝床上。煤气罐靠墙放在门内,在门框上打了个眼,将煤气管通到门外,连接在煤气灶上,煤气灶放在房门外面靠墙的楼道里,我们就在楼道里做饭,水房在二十米之外。我们母子俩在这十六平方米的单身楼房间里度过了近两年的光景。随着工厂的军转民进程,工厂在西安东郊又建了新的基地,我们母子俩又一起来到了西安东郊。我爱人在西安东关南街的一个电器厂工作,还算是这个厂吸引来的人才。这个厂在办公楼的四楼给了我们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这个房间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后就转不开身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还算是好的。可是东关南街离我们上班的工厂新基地幸福北路很远,孩子又没有幼儿园托儿所可以送,因此,我们只好在我们工厂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我和孩子住在工厂附近,我爱人来回跑着。这样我上班就会方便一些,孩子也可以上我们工厂的幼儿园。租的房子还没有来得及粉刷,我们就急不可待地搬了进去。
这一住就是两年,那两年我深刻地体验了租住民房的酸甜苦辣。
我的房东共有上下六间房,我们一家三口住一楼靠西的一间房。房间十八平方米左右,我们用大立柜将房子隔成了两个区域:大立柜后面安放着床,是我们住的地方;大立柜前到房间门的地方放着沙发桌子什么的,是一家人吃饭活动的地方。房东把东边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下的空间也送给了我家,我们用来做饭。房东两口外加两个儿子住一楼中间以及东边的一间,二楼住的是我们工厂的其他两家和铁路局的一对年轻夫妇。房东夫妇倒是和善的两口子,两个儿子也甚是可爱。院子靠大门处有公共的水龙头可供院内住户洗菜洗衣,一院五户十余口人倒是相处和谐,只是到了做饭用水时很麻烦,你端着青菜、他端着米和切好的土豆丝排队等着过水,每个人都显得礼貌而有涵养,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谁也没有显得比谁急一些,但是手里端着要洗的东西站着等着的人,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了水龙头。这洗衣洗菜洗锅每天每次的等待对于上班赶时间的我来说,实在不方便,甚至有些饱受摧残的意味。但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这个城中村出租院子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村里百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距离我们还有两条街大概一公里左右,而且还是旱厕,冬天倒还罢了,夏天臭气熏天,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带孩子的人了。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每天穿行在这个村的大街小巷,脑海中不时就冒出了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这个声音在我心底鼓噪得时间长了,我就想如何才能得到工厂的母子间呢?俗话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想着想着,这个目标就渐渐列入了我的生活规划中,我就动了要工厂新基地的母子间或者过渡楼的心思。
新基地西安厂区的母子间可不像西沟老厂区的母子间。
西沟厂区的母子间是一栋专门的母子楼,每户都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就是小一点,但好歹是一室一厨一卫的房子。可新基地的母子间是单元房,比如两室一厅或者三室一厅,一个卧室里住一户,两室一厅就住两户,三室一厅就住三户,大家共用客厅、卫生间和厨房。当时工厂也有过渡楼,就更方便一些,类似小一室一厅,有单独的小卫生间小厨房,卧室外有阳台。但过渡楼入住条件更高,有的是分给了不符合分两居室单元房的双职工,有的是分给了工龄长的带孩子的单职工。虽然不是正经分配的两居室一居室,但也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这就成了我为了解决租住在城中村不方便的问题而寻找的最新目标。
我当时是工厂一个综合科室的科员,我和爱人找了房管科科长,提出了想租住工厂母子楼的想法。几番周折,过了两个月,处长出面约了房管处的处长、房管科的科长吃了一顿饭,给工厂提了吸引人才的租住过渡楼的方案。我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本科生人才就获得了用每月八十元的租金租住工厂过渡楼一室一厅的居住权。我和儿子在拿到过渡楼房门钥匙的当天就急不可待地去打扫了卫生,也没有粉刷,第二天就将租住的民房里不多的东西搬了进去,终于摆脱了在城中村租房住时难上卫生间、洗衣洗菜时共用水龙头、一年四季在楼道下逼仄的地方做饭不小心就能碰着头的日子,终于有了自己的虽小但厨房卫生间齐全的住处。老公做了一个能用电加热的水箱架在了卫生间顶端,也解决了租住民房时的洗澡难问题。我们一家住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很难忘的日子。
在这小小的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我隔三岔五地接待我的姐妹们,又给六十多岁患了绝症的婆婆看病治疗,这个小家甚至一度成了我老家人来西安的落脚点、联络站。除了偶尔用水高峰时水上不来需要存水外,这个在六层的过渡楼确实解决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孩子上幼儿园的地方就在我们楼的几栋楼之外,接送也方便了许多。我同时也认识了不少同年龄住在这个楼的工厂同事,扩大了社交圈,直到公司开始进一步房改。
双职工用分排队交八千元左右就可以分一套两居室或者三居室的房子,楼层位置什么的也是按分数排名先后选取,这恐怕是许多六〇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共同记忆。我们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宝鸡的山沟往西安搬迁,就牵扯到五千余名职工的吃住问题。工厂的住宅区基本建好后,工厂就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就陆陆续续地分房。许多资历老的职工都住进了新房,我们那一拨入厂的学生,两口子都在工厂上班是双职工的也有许多都分上了房子。估计当时工厂新建的房子有剩余,或者入职工厂的大学生不都是在自己的工厂找对象,有些和我一样,在外面找的对象,这些人的分数就很难达到工厂分房的标准,但也有住房诉求。
一次工厂的厂务会研究:符合已婚本科的条件,一次性交够六万元的房子成本价,就可以购买厂里盖好的六十平方米的两居室一套,离异的属于单职工的有孩子的本科生可以交两万元购买一套两居室。政策公布后,有些像我一样的单职工大学生就面临着选择:是享受购房政策提升居住条件呢,还是凑合着住呢?是在现有条件下交六万元购房呢,还是离婚后交两万元购房?选择这时候就摆在我们面前,在一个月的考虑期内熬煎着我们。我们的孩子这时已经七八岁了,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有时和我们挤在一起,有时在过道或阳台上支个单人床自己睡,搬来搬去的非常麻烦。有同事怂恿我们俩开个离婚证,用两万元购买一套房住,但还像没有离婚一样一起过日子。我寻思来寻思去,觉得这样做不符合我的三观,这样做的话我就会变成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就没有起这个念头。但又想改变居住环境,怎么办?在当时的情况下,路只有一条,就是筹够六万元交到工厂的财务处,然后等着分房。
1996年9月6日,我提着装有六万元现金的纸袋子坐上从西安到老厂区宝鸡蔡家坡的工厂通勤车时,满怀壮烈,激愤和悲壮的情绪一路冲撞着三十一岁的我,平时像活宝的我这天一路无语,听见同车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事为交两万元的房款一路骂骂咧咧,我在心里轻蔑地笑了:你那算什么?
我要交六万呢!1996年的六万元人民币对一般家庭来说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两口一开始就六万元买这个房子也是意见不统一。最后还是我老公公认为现钱放在手里,不知不觉地就花完了,也不见什么效果,如果压力不大,再借少量的钱能改善住处,能给娃提供一间独立的房也是一种好的选择。一锤定音,我们就东拼西凑了六万元,由我坐车去宝鸡老厂区财务处交付。
班车行驶了四个小时,到了位于宝鸡蔡家坡的老厂区。
我提着装有六万元现金的纸袋去财务处交钱,财务处的会计人员一再确认我是否要交,问得我心里都没有了主意,又给我老公打电话,老公说交了吧。那天我所在的处室支部也正好要开会研究我的入党转正问题,会后我们处长听说我要交钱,也一再叮咛我想好了。我被人问得六神无主,又去给老公打了一个电话,说厂里的人都议论我是神经病,那么多的钱干什么不好,非要交到厂里购买一套不知什么时候能到手的六十平方米的两居室。老公听后说,定了的事就定了吧,还是交了吧,这样至少有一套房子住,娃大了,上学也方便。打完这两次电话,我就义无反顾地去财务处交了购房款,坐下午的工厂班车回到了西安。班车开了一路,一路上车上的人说什么我也没有听到,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回响着《骆驼祥子》中的一句话:我把多年的辛苦交给了人,我把多年的辛苦交给了人,我把多年的辛苦交给了人……回到家,我跟失了神一样,直接昏睡了一天一夜。
最后得知工厂当年享受这个大学生骨干购房政策的并交了六万元的就我一人,也有人离婚了享受的是两万元购同样的房的政策,因此,我当时就在工厂落得了一个富婆和神经病的双重外号。因为这类人就我一个,我交款后没有多久,我们处长就告诉我哪儿哪儿腾出了空房,鼓励我找工厂分管后勤的领导要房。1997年我终于分到了一套别人腾出来的两居室。
我们把这套来之不易的房子认真地装修了一下,找了个黄道吉日就搬家了。其他的细节我也忘了,我只记得我儿子当时已经整整九岁了,到了新房,跟刚放出场的小马驹一样,这个屋那个屋地撒着欢跑……我人生中正儿八经的第一套房,留下了我们家多少珍贵的、感人的、伤心的记忆啊!
2004年,我们公司因为扩建北迁西安高陵,在公司配套的小区,我购买了一套面积更大、功能更齐全的双层复式房子,装修入住后我的孩子也考上了大学,以前位于西安幸福路老厂区的这套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就失去了居住价值,但家里谁也舍不得出租和出售。儿子说,这里有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是啊,他从这儿上幼儿园念小学、初中,从这儿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国门,有多少美好的憧憬和向往都是在这儿产生的啊!
后来不管是出于投资还是出于改善,我还购买了不同地域的两三套房子,但是,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搬进不到三十平方米的过渡楼时的欣喜若狂的感觉,再也找不回当年住过渡楼和两居室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想,对于房子而言,每个人适得其所,房子也才算是物尽其用了。
不想过年
时光飞逝,1996年转眼间就到来了,又到了阖家团圆、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时候了。可是近“年”情怯,我怕过年,也不想过年。
前些年不想过年是因为过年要串亲访友,要给小侄儿小外甥准备压岁钱,当时囊中羞涩,一元钱当两元钱用,日子比较难熬。
近两年工资水平提高了一些,倒不必为压岁钱及过年的礼物而发愁,可是仍然不想过年。前年过年,我的生父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生苦短,失去的不可能再得到。又过了一年,我的婆婆离开了我们,使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时间的威力。短短的两年时间,亲人走的走了、老的老了,这个世界上关心我呵护我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有时想,不过年多好,那样时光就不会飞逝,所爱就不会离开,青春就不会老去。
不想过年,不想看见母亲鬓角一年比一年增多的白发;不想自己事事无成而眼角的皱纹却增加了一道又一道。不想过年,不想听见时间急促的嘀嗒声,它使我感到了慌张和不安,使我来不及仔细地欣赏四季的风景,来不及注视丈夫日夜操劳脸上挂满的疲倦,来不及观察儿子一天天长大的细微变化。再回首,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日子就在抱怨声中滑落了。
三十多岁了,才发现“年”的脚步是那样匆匆,全然没了童年时的温馨和香甜。小时过年,能吃上平常吃不到的可口年糕,能在除夕之夜,反反复复地翻看枕头下压着的装有五角或一元压岁钱的新衣服,盼望着天快快亮。现在每逢年近,却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是不是人未老,心境却老了?
我不断地自我反省,忽然想起很早的时候看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下联是“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仔细琢磨这副对联,才发现古人早已有了不想过年、过年难的感受,并把这种感受提炼成了一副富有哲理的对联。看来,生活从来就是在矛盾中螺旋式地向前行进着,从古到今谁也挡不住它那从从容容的脚步。那么何必要一味地逃避,一味地沉浸在叹息和失意声中?何不在年末岁首来一次精神上的除尘洗涤,洗去那消极等待、患得患失的心绪,保持一个清新平和的心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
想通了,“年”就不那么可怕了,也可寻到它那独特的魅力。年到了,树叶该绿了吧?花快开了吧?儿子个子也该长高了吧?
起心动念
最近看了一本名为《天地感应篇》的书,对“起心动念”这个词有了新的体会。书上讲,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慈悲善良,并不是看你做成了几件善事,关键是看你起心动念时的善心慈悲心有多少。
人的能力地位不同,所能做的服务众生的事就不同。只要你念头是好的,是出于公心为众生服务的,而不是自私自利只想到自身的,这就可以算作善。而不是说你有慈悲心而没有实现,上天就忽略了你的善;你行动上做了几件善事而内心恶贯满盈,上天就看不见你的恶。因此,我对“慎独、修行”四个字就有了全新的理解。
想起有一年去台湾,参观星云大师的道场佛光山佛学院,最有印象的就是他的“三好”的理念: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其实与《天地感应篇》上说的善心、善举,本质上的意义一样。
二十七八岁时,有一次坐火车从宝鸡蔡家坡回西安家里,火车过了咸阳站,眼看着再有十来分钟就到家的时候,却突然临时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