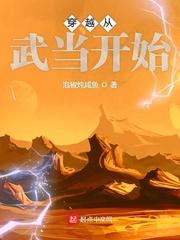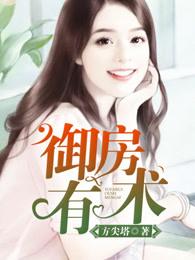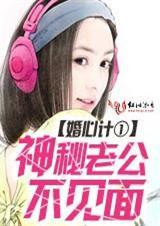456小说网>远道而来的客人祝酒词 > 坚硬里的柔软(第2页)
坚硬里的柔软(第2页)
我们都在追求完美,岂不知道,真正的完美,我们无法接受。早些年,我们在宣传英雄人物、模范典型时,一味进行拔高、美化,没有儿女私情,没有毛病缺点,人物形象扁平化。没有立体感,就不是活生生的人。没有血肉的人,只能是一具没有生命的骨架。恰恰因为这种打破,带给牌匾一种独特的美感。
篆书,无论是大篆还是小篆,都有金石之气,但难以看懂。就像一位修为高深的道人,只能膜拜,无从交流。楷书太正,过于严肃。草书,行云流水,缥缈之味过甚。隶书,满足了我对艺术与人生的双重想象。古朴又灵动,秀气又方劲,雄放又端庄。我固执地认为,书法中,隶书是最生活的艺术。隶书,有“汉隶”之称。在我看来,隶书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书法艺术最为坚实和成熟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隶书可能象征着最纯正的华夏文化,属于本土文化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我偏爱隶书。练习书法,成为书法家,天赋是不可或缺的。敬畏书法,敬畏我们的文化,只需要我们的真诚和执着。
牌匾从大小到色彩的选择,再到这隶书,都有低调奢华之感。
西大街虽比不上大城市街道的繁华,但更丰富多彩些。仅仅是路人的着装,就令人欣喜。大城市的装束,流行的服饰,这儿全有。这儿还有回族人的白帽、黑头巾,藏族人的藏袍、高靴,喇嘛的僧衣,明代风格鲜明的尕娘娘服饰。边塞的西大街,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T型台。这些牌匾,不怯懦,相当自信。它们像店铺的眼睛,一双双柔情满满的眼睛,似平静又幽深的水潭。西大街,因有了这样的牌匾,寒风凛冽时,也就有一束束温暖的目光。
黄昏时分,晚霞满天,这些牌匾似乎多了几分羞涩,又像在点燃某种情绪。暮色之后,它们先是躲在五光十色、有些妖娆的霓虹灯身后,而后回到自己的黑暗中,咀嚼一路走来的滋味。它们来到高原,远比我早,我尚没有达到它们这样澄静、如禅的境界。与它们相比,我在漂泊中丢失了太多的东西。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偶尔想起自己曾经的模样。
孤独时,我会想起这些牌匾。想起这牌匾,我总会想起家乡:抓一把桑叶喂蚕,看一群小鸡在老母鸡后面排成队;村口的老槐树浸在晨曦里,从树叶间洒下的阳光,如同半梦半醒的我;河边的芦苇中,鸟儿在鸣叫,燕子从水面掠过;炊烟离开黑色的屋顶,飞向辽阔的天空。
有时,我会走近这些牌匾,默默注视片刻,目光沿着那些笔画游走,转折,舒展。它们是静止的,我也静静站着,而一切又像是涌动不息的。有时,我还会向右看牌匾,向左看车流、人潮。有时,车流、人潮凝固了,牌匾在漫步。
与这些牌匾相处,我在为自己的灵魂按摩,又在倾听临潭的心跳脉搏。
五
大坡桥桥头的牌楼正对着一条小马路。是的,我的第一印象,这就是一条铺着沥青的、窄窄的马路。路面渐渐高起,没多远,就进入山里。然而,我没走上几步,就仿佛进入了一条古街。
这给予我巨大的错觉。我又在这样的错觉中渐而愉悦起来。
路两旁的房子,不是店铺,是普通人家的住宅。木门、铁门,都是仿古的,虎头门环尤其引人注目。小小的门楼,青砖砌出向外挑的檐角,顶上覆瓦,刻有花鸟鱼虫。院墙顶也覆有青瓦。远处的山顶,如同一个孩童趴在墙头,顽皮中还有些深沉。有些门前,还有一对石狮子,间或夹在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的房子间,反倒像受气包。那些树,也有江淮的风范,不高,较粗,树冠展得很开,许多树叶抱在墙头依偎在墙面。阳光下,树叶好似河面上的水波,波光粼粼。时不时有鸟儿从树顶飞过,枝叶间的鸣叫,是那样动听。在一棵树上,我还发现有一个硕大的鸟窝。在临潭县城里,如此高大的树,实属少见。它们没有受到景区里的树那样的优待,只和平常人家生活在一起。虽在马路边,但如同村口的老槐树一样淡泊。村口的老槐树,挂满乡愁,反反复复地走进游子的梦里。我相信这里的人们外出闯世界,在异乡是会想念这些树的。
这里的房子,有的年头不短了,个别的还是斑驳的土墙,称得上“爷爷辈”的。以时间为序,这些房子就像四世同堂的一个大家庭。背靠大山,紧邻县城,它们默默地守护和传承,维系着一种与血脉相连的依恋。我能想象,这里的居民既享受了现代文明的福利,又没有迷失自己,终是活出了自己的惬意。
低调,并非故作的姿态,而是内在饱满的自然举动。面对中高档的现代住宅小区,这些房子不倚老卖老,不自卑,与世无争,把江淮文化过在日子里。它们留住江淮之风的繁复之韵,让我一解乡愁。说是繁复,其实与时下的建筑相比,它们反倒简洁。那些精致的线条,那些看似层层叠叠的图案,因为如生命般流畅,反而无审美疲劳,很是提神醒脑。倒是现在的一些设计,总给人以错乱之感。我以为,现代人的焦虑症,与自我营建的环境大有关系。这也许就是一种作茧自缚。
原生态,是向生命本原回归的情境。建筑文化的原生态,还是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性关系。房子,是用来遮风挡雨的,也该是人的一部分。房子,是身体的扩展。因为欲望的狂热,我们总是忘记了出发的原因,扭曲了生活的种种。我们猎取得越多,就越发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现在的房子越来越高级,但总是缺少了一些人情味。
住在这里的人们,走出家门,加入世界的喧哗,为稻粱谋,难免与浮躁、焦虑为伍。归来时,身心回到宁静之境。我相信这一点。漂泊在外的人,故乡在远方,回家的路漫长而艰辛,只能终日怀抱乡愁的忧伤。而他们只需拐个弯,就能轻易切换生活的节奏、人生的境况、心灵的空间。对他们而言,天地之间,只有地平线那一条线宽度的距离。更何况,满天的星星还能照耀他们的睡眠。
他们是幸福的。
在县城西门桥附近有一条小街,当地人称为“背街”,以批发小商品为主。街面很窄,容不得两辆轿车会车,只有摩托车、电动车和小三轮在人群中穿行,像水中的鱼一样灵活。这里的许多铺面还是木质结构。早上,店主卸下一块块门板开张迎客,晚上关铺子时再装上一块块门板。白天,这一块块门板像铺子的伙计一样站在门边,脸上现出岁月的光泽。现在许多所谓的古镇正在新建、打造这样的古味,而这里是时光酿造的古味,有真正的岁月味道。
慢时光,来到我身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就像置身于旷野一样无拘无束。放下一切沉重,远离生活中的阻碍,像河水一样轻抚松软的河岸。我没有喝茶,但喝茶时的心境萦绕着我。我坐在一家开门的店铺前,背靠木板,盘起双腿,微闭双眼,后脑勺挨着木板,收回听觉。有那么一会儿,我的灵魂似乎飞出我的肉身。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与草垛相处的情形。村里的晒场,是我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草垛。我爱爬上草垛,尤其是在傍晚时分。白天,阳光太烈;夜间,太黑,我有些怕;傍晚,天空最为奇妙。我躺在草垛上,什么也不想,只把目光投向天空,有时也眯起眼,告诉自己睡着了。长大后,当我心烦气躁时,常常找棵树坐下,回想儿时躺在草垛上的画面。这对我是极好的心理治疗。
街上行人、车辆不算少,可我还是觉得很安静,很清爽。有位老人坐在格子窗下,那小小的板凳似乎比他的年纪还大。一杆烟锅,长度快赶上他的手臂。烟锅头黝黑,里头装着金黄的烟丝,烟锅杆油润润的。老人一手端着烟锅,一手轻抚胡须。他的胡须很长很白,就像电影里那些常见的特写,有仙风道骨之气。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大概是他的孙子,在他身边独自玩耍。格子窗,一半在阴影里,一半在阳光下。
这一切与整条街,既浑然一体,又完全独立。
我当然在他们的世界之外。
六
我喜欢图书馆的氛围,更甚于读书本身。
曾经看过世界十大最美图书馆的图片,那是读书人的圣地。如果真有天堂,这些绝美的图书馆,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
读书,是一件可以也应该让人忘记一切的事。因而,那些在特殊境地中阅读的人,总能发出迷人的光芒。列车上,窗外的景色如时光飞逝,一个人靠窗而坐,翻开一本书,逆光的效果,仿佛折射出看书人清纯的灵魂;嘈杂的街头,一切都是骚动的,一个人捧着书坐在台阶上,风吹书页微微颤动,如醉在阳光中的荷花。他坐在人群中,又似乎坐在世界的尽头。这是经典的阅读场景,也是人书合一的天地大美境界。静心阅读的人,是最美的。
阅读,有一个好去处,自然更妙。一座城市的图书馆,理应是最具仪式感、最具信仰的文化场所。图书馆,安放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精魂。我对图书馆有着异乎寻常的期待。即便如此,临潭县图书馆仍让我大感意外。这个图书馆没有单独的楼,而是与文化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挤在一幢四层的楼里。这倒像一家人住在四合院里,一份深入骨髓的亲情,或明或隐地流动。这四个馆——文化长路上的四个重要驿站,在相互取暖中,坐而论道。
令我惊喜的,是馆里的古籍阅览室,一个极具明代风格的大书房。木质书架,完全仿制明代款式。榫卯结构,守住的是精巧智慧的文化。原生的木纹,清透的水漆,依然带着森林的呼吸。线装书和珍贵的老版本,与这样的书架依偎在一起,高古而凝重,洋溢着某种神秘感。我在书香中迷失了,傻站了许久,没敢动一本书。我没有准备阅读,我认为随意取一本,轻佻地翻翻,那是对它们的亵渎。我不能容忍自己在书面前放肆。
高原强烈的阳光,经过窗玻璃的过滤,铺在桌子上时,温柔了许多。轻便而不失骨感的太师椅,容不得我懒散。我坐得笔直,仿佛腰椎比平日抻长了一些。我的目光总离不开书架和那些书。一个个文化巨匠,一个个学术大家,向我走来。
书,是用来读的。可我总觉得,有些书可以不读,让其静静地坐在书架上,卧在案头。我的心与它们无声交谈。有些书,只能敬畏,不可轻易走进,一旦打开它,就不能怠慢。因为有如此经不住推敲的怪念头,有数十本书,我很早就请回来了,但一直没敢读。
在写作的时候,我可以不看书,但如果身边没有书,我就有些失魂落魄。我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但如果很多书在我身旁,我总能感觉得到它们的神力,写作竟然顺畅很多。我曾经在图书馆工作几年,一个只有十来万册书的小图书馆。那时候,我利用身为馆长的便利,午间常钻进书库,搬一把椅子坐在高高的书架间。不是看书,是以打盹的方式进行午睡。我自以为是地觉得,在书的丛林中入梦,相当于我在阅读它们。这当然毫无道理。但我在醒来时,往往感觉充实许多。
梦里读书,或许只是一种滑稽的想象,可能还是我为少读书所作的辩词。但,环境的确可以感染人。我坐在这样的阅览室里,只是静静地坐着,就有与阅读同样的愉悦。墙上的砖雕,工艺有些粗糙,恰恰因为这种粗糙,才有了古拙的质感。有一块砖雕,图案是莲花。莲是高洁的象征,也是华夏文化极其重要的一种象征。这间阅览室的陈设,本身就如高原上的一朵莲花,不是雪莲,而是江淮池塘里的青莲。
此刻,砖雕上的莲花与书架和书,都在诉说优雅的文化时光,似甘甜的泉水,滋润我风尘中干渴的心。明暗的光线,让莲花格外立体。亮处,柔光润泽;暗处的线条,硬实而不失灵气。窗户正对着一所中学的操场。身穿校服的学生,有的说笑打闹;有的独自一人走在跑道上;有的捧着书,或走,或坐。侧耳细听,一个女学生的读书声传进我的耳中。浓重的临潭口音里,那些零星的江淮音节,有细雨落在水泥地上的清脆与酥软。我听到的不是乡音的闪烁,而是这位女学生呼吸里的江淮气息。
馆里的工作人员端来一杯茶,说是今年陇南的新茶。青花瓷的茶杯上,也是一朵莲花。这莲花比砖雕上的更加秀丽、灵动。我的视线漫游在这鲜艳的色彩里,居然生出绵软的光影。我知道这是想象。我喜欢这样的想象,喜欢这样助我思绪飞翔的氛围。
恍惚间,我看到,有一种情怀,走过青稞地,坐在高原的山顶。迎面而来的风,吟哦田园诗意。
有一天,我去羊永镇卫生院。那里的中医馆,同样让我眼前一亮。我拍了几张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让朋友猜是什么地方。当然,我故意回避了那些明显的标识。有人说是饭店,有人说是图书馆,竟然还有人说是候客厅。其实,这小小的中医馆,也就是乡卫生院的一个小专科室,并没有做多少花头的装修。他们只是以漏窗、木格稍稍做了点缀。只不过心意用得正、用得细,把中式风格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里的人们啊,外形的粗犷与内心的细腻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建筑风格上,他们做得如此内外兼修。如此一来,风格一词用在这儿并不精确,用“气质”,更为贴切。江淮风,也不再只是一阵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与灵魂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