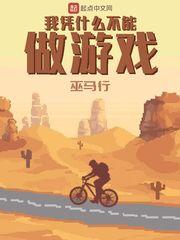456小说网>雪祭司 > 3(第2页)
3(第2页)
连长没有说话,只有尿尿的声音。
稍后,连长说:“我本来不想提前告诉你,但是现在还是告诉你吧。
听说志愿兵提干指标快下来了,你年龄也不小了,也许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犯糊涂,因小失大……”
刘铁说:“我得罪过陆海涛,他不会给我说好话的,我早就不抱啥希望了。再说,秀芸怀着孕呢,要是她和孩子有个闪失,我就是提了干又有啥意思?我已经失去太多了,我不想再对不起秀芸!”
连长说:“可是你下午去找老陆请假,他不是没同意吗?”
“他这是故意刁难!”
“也不能这么说,他也是为了工作,最近确实很忙嘛。”
“你别说了,我自有办法,不会让你为难!”
“你这驴脾气,可千万别胡来!我再想想办法……”
两人走出厕所,后面的对话听不清了……牛大伟仰靠在床上,眼睛盯着被雪水弄出地图形状的帐篷顶,开始琢磨这事。前几天听人说,陆副主任最近正在给团部物色一个放映员。电影队只有两个女兵,下部队放电影搬运东西、挂银幕不方便,需要一个干体力活的男兵。如果能进团部当放映员,不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吗?放电影既轻松,又干净,还能天天看电影。关键是还能天天跟女兵在一起,那可是多少男兵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在团部轻松混上三年,也就复员了,多好的事啊。听老兵说,陆副主任权力可大了,选调放映员的事他说了算。所以,牛大伟一直想跟陆副主任套近乎,可始终没有找到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要是把昨晚在厕所听到的那段对话告诉陆副主任,他一定会感兴趣。说不定他现在还不知道刘铁逃跑下山的事呢。在七连,除了他牛大伟,估计也不会有人去向陆海涛汇报这种事。连长赵天成在七连根深蒂固,官兵们遇事都向着连长,陆副主任早就被架空了。如果这个时候去向他汇报,是不是有点表忠心的意思?如果因此得到了陆副主任的信任,去团部当放映员的事情就没问题了。
好,就这么干!宁愿当一次小人,也要离开这鬼地方!牛大伟迅速起床,穿上大衣,从床底下的携行包里取出两条“红塔山”,裹在大衣里,低头钻出了帐篷。
陆海涛单独住在一顶帐篷里。这顶帐篷跟营区其他帐篷别无二致,只是中间用帆布隔开,外间放大米面粉土豆白菜,里间住人。外间存放蔬菜,不能生火。里间住人,不生火夜里会冻死。雪拉山冬天最冷的时候,能有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现在夏天来临了,但夜里仍有零下二十多度。里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木桌。因为连队老搬家——筑路部队就像候鸟,总是搬来搬去,这段路修好了,就得搬到下一个施工点去——木桌已经破旧不堪,桌面油漆斑驳,陆海涛嫌难看,在上面铺了一块旧的军用绿毯。桌子靠外面的那条腿有些活动,用铁丝拧着。一个火炉占据了很大空间,火炉旁边有一个装罐头的木箱,但里面没有罐头,放着块煤。没有块煤的时候,放些牛粪饼。
冬天大部分时间,连队都跟附近的牧民一样,烧干牛粪取暖。火炉上面是铁皮烟筒,两米多高的地方弯成直角,朝帐篷外面延伸。因为烟筒比较长,中间就有些下垂,便用一根铁丝吊在帐篷顶的铁架上。下垂处滴答着黄色的烟水,下面挂着一个绿色的空罐头盒接着。每隔几天,通信员小刘就会把罐头盒取下来,倒掉里面的黄水,然后重新挂在那里。帐篷有四个窗户,外间两个,里间两个,窗户不大,上面钉着塑料纸。夜里一刮风,塑料纸啪啪直响,像鬼拍手。塑料纸上戳有几个小洞,这是为了减小风力,使得“鬼拍手”的声音小点,还可以通风,防止夜里煤气中毒。但即使如此,“鬼拍手”也会影响陆海涛的睡眠。所以早上起来,他的眼睛总是红肿的。
这顶帐篷原来是炊事班的储藏室,司务长住在里面。陆海涛来了之后,为了给代理指导员腾地方,司务长搬到炊事班的帐篷里去住了。按说陆海涛作为代理指导员,应该跟连长赵天成、副指导员杜林一起住在连部的帐篷里,但陆海涛说他在机关写材料熬夜熬惯了,睡得比较晚,有些神经衰弱,怕影响别人休息。其实他不是怕影响别人,而是怕别人影响他。他知道赵天成睡觉爱打呼噜,而他睡眠一向很浅,一有动静就会醒,一醒就彻夜难眠。
还有,由于卫生队医生黄雪丽的原因,他觉着跟赵天成住在一起,多少有些别扭。
尽管陆海涛不出操,但他从来不睡懒觉,早早就起床了,叠被,洗漱,喝一杯温水,利用早操和早餐这半个多小时,看几页书。陆海涛的被子从来不让通信员叠,都是他亲自叠,叠得一点不比战士们的差。他也从来不让通信员给自己洗衣服,也是自己洗。这一点他感觉比赵天成做得好。赵天成从工地一回来,把脏兮兮的衣服一脱,往旁边一丢,通信员便赶紧拿去洗了。
陆海涛有次提醒赵天成,要官兵一致,自己的衣服应该自己洗。赵天成半开玩笑地说,官兵一致?能一致吗?你穿“四个兜”,战士能穿“四个兜”?
你一个月拿多少工资,战士们一个月拿多少津贴?再说,连长有连长的职责,通信员有通信员的职责,洗衣服就是通信员的职责之一。我要是天天洗衣服,谁带大家上工地,谁指挥大家施工?赵天成的言外之意是:你又不上工地,天天待在营区帐篷里,当然有时间洗衣服。陆海涛心里很不舒服,又不好说什么。
牛大伟在外面喊“报告”的时候,陆海涛正坐在桌子前看一本厚厚的有关西藏的书,旁边放着通信员没有来得及收走的碗筷。陆海涛突然被打断,有些不悦,冲着门口说:
“进来!”
牛大伟穿过外间,撩开帆布帘走进里间。
“首长早!”
陆海涛把目光从书上移开,扭过头来,用一双红肿的眼睛看着牛大伟。
“什么首长?我讲过多少次了,叫指导员!”
“是,指导员!”
牛大伟红着脸,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起怀里揣着的“红塔山”,忙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好像那不是烟,是炸弹。
陆海涛瞥了一眼桌子上的烟,说:“红塔山?档次不低嘛。”又突然把脸一沉,直视着牛大伟,说:“你胆子不小,大白天也敢来糖衣炮弹!”
牛大伟不知道陆海涛是装清高还是真生气,心里有些紧张,但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说:“首长,烟酒不分家嘛。”
“又叫首长,叫指导员!”
“是,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