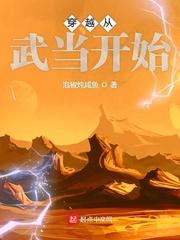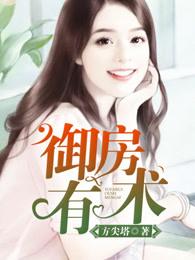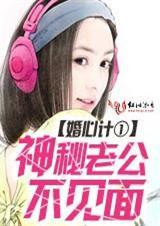456小说网>雪祭司 > 后记(第1页)
后记(第1页)
这本书仍是写西藏。我十九岁开始进藏,三十年先后四十余次进藏。西藏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我一次又一次迎着漫天飞雪,一路仰望,沿着我们自己当年修筑的天路去西藏。这些年里,我为西藏“生”过五个孩子:《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西藏,灵魂的栖息地》,还有现在这本《雪祭》。
《雪祭》是我孕育时间最长、最难产的一个孩子,我差不多孕育了她二十年,“生产”时的阵痛,比其他孩子更加痛彻心扉。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这些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笔宝贵财富。我将这些劫难概括为七种死法: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四十多度,我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五十八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我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我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我几乎被砸死;我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我几乎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我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们几代西藏军人的!这些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几年前,由于部队需要,我调离高原边疆,来到渤海之滨辽宁任职。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就像拉紧的橡皮筋,距离越远,拉力越强。西藏使我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站在零海拔的地方,仰望高海拔的灵魂,总也忘不了那些西藏往事。忘不了进藏路上那些朝圣者虔诚坚毅的目光;忘不了长江源头、雪山之巅的壮美日出;忘不了唐古拉山口的满世界的皓雪;忘不了老班长接到女友分手信时的那种绝望与悲伤;忘不了一个新兵从兵车上跳下来,双脚刚刚踏上千年冻土,却因高原反应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给中断时,一个战士为了追赶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随即倒在了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忘不了体力不支时,排长端给我的那碗白糖水和藏族同胞送来的酥油茶;忘不了阿里无人区里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时,难以控制的泪水;忘不了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忘不了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丈夫去执行抢险任务,母子在营地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忘不了被樟木口岸“三百米死亡线”、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线“102”
塌方群、“怒八”山体大崩塌吞噬了的那些战友;忘不了我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亮,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又帅气的代理排长,一点一点停止了呼吸;忘不了一个推土机手连同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瞬间卷走;忘不了川藏线上那个爱笑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半个月后我们才找到他的半具遗体,三个月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1982年,我们八百名陕西兵(包括几十名西安女兵)踏上了西去的绿皮车,走上了青藏高原。我们八百人里,后来有的牺牲了,有的留在西藏工作了,更多的则退伍转业了,现在还留在部队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当兵之初,我们的任务是将慕生忠将军开辟的青藏公路毛路,改造成为二级柏油路。后来,我们又转战黑昌线、川藏线、中尼线、新藏线,足迹几乎遍布西藏。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就晕倒了,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后来翻越的次数多了,渐渐有了抵御高原反应的能力。有一次,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块写有“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让战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我在背面写下一句话:“唐古拉就在我脚下!”
当年修筑青藏公路时,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哪些是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悄悄掩埋。老兵说,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从那时起,我感觉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有了生命,有了跳动的脉搏。进藏的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三十多年来,每进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一次洗礼。
这部书的时间跨度大约六十年。去西藏多了,便对西藏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慕生忠筑路大军、康藏筑路大军,以及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等等。当年慕生忠带领的那支奇特的筑路大军里,有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还有一些国民党投诚官兵,后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结局可想而知。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富平县上千名新兵走进西藏,他们后来参加了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百多人牺牲在了西藏,他们的忠骨至今还埋葬在遥远的那曲和泽当等地。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都听人讲起过,我还专门做过采访调查。一代又一代西藏军人,为了建设西藏保卫西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二十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但不写出来,始终是块心病。2013年底,我离开边疆后,对边疆的情感更加浓烈,感觉再不动笔把这些事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战友。我用了一年时间打腹稿。2014年秋天,我有二十天去三亚疗养的假期,在那个零海拔的地方,我一口气拉出了初稿。2015年整整一年,我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年底前完成。我习惯晨练时打腹稿,这个时候思维最活跃。
为了恢复被高原损害的身体,我坚持每天六点起床锻炼。锻炼时,兜里揣着笔和纸片,有了想法就随手记下来。在三亚疗养时也是这样,早上锻炼时想好,回去再落实在电脑上。走在零海拔的海滩上,不由得会想起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有的战友直到牺牲也没有见过大海。
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许多人都误以为我是专业作家,我每次都纠正:我是职业军人,业余作家,我的水平很业余。我平时忙于工作,只是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画画。书中的插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封面的题字也是我自己写的。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别人家过年有姐姐剪窗花、贴窗花,我没姐姐,我家没人剪窗花,我只好拿起画笔画窗花。我画南瓜,画玉米,画鱼虫鸟兽……我写字画画也很业余,无宗无派,与天为徒,师法自然。人在军旅,东奔西走,三十余年转战六省,没有时间拜师学艺,只能抽空读帖品画。这样也好,博采众法,归于无法。我以为,无论“师古人”“师造化”,皆应“师心不师迹”。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话很有道理,我很喜欢。字画讲究的是笔趣和意境,强调一个“魂”字。书中插图,在行家眼里也许不够水准,但皆“发我之肺腑”,画的是我眼中的西藏,心中的西藏。
长眠在雪山的战友们,我捧一把雪祭奠你们,我用一本书祭奠你们!
党益民
2016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