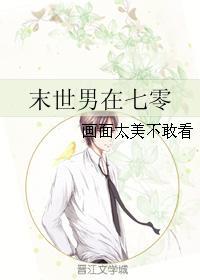456小说网>大清帝国国旗 > 第二章 经济制度的变革(第2页)
第二章 经济制度的变革(第2页)
康熙时期还治理了浑河,该河泥沙量大,有“小黄河”之称,泥沙使河道淤塞,导致下游常遭水灾。康熙年间挑修了一条长二百多里的新河道,将河水引入海中。从此以后,浑河安然,改名永定河。
雍正、乾隆时期,在重视治理黄、淮的同时,对江浙沿海的海塘也加强修固,为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明末战乱,清朝建立初期,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在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农业生产逐渐走向恢复和发展。
这时期农田面积大大增加,水利得以兴修,商品经济在农业中有一定的发展,这些都为清王朝兴盛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奏销册统计,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南等地的耕地面积比以前都有一定的扩充。山东、河南比顺治时期各增约200万余顷。江南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95万3000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100万顷,乾隆十八年(1753年)为150余万顷。抛荒最多的四川地区,顺治十八年才1万余顷,到乾隆十八年已增至45万9000余顷。
清统治者还采取了种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鼓励农业发展,奖励垦荒。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更是宽大。鼓励少数民族垦荒,这对当时耕地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恢复都起了一定作用。如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尽管清朝政府实行封禁,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挡关内人前去开发。新兴城镇吉林,康熙时“已有中土流入千余家”,到乾隆四十六年,旗地、民地加在一起达35000多顷。内蒙古地区,由于大批汉人进入,沿长城一带逐渐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山东人尤其多。新疆就北疆而言,根据乾隆42年的统计,各类屯田已有56万7000多亩。台湾的开发更快,因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闽广“漳泉粤东之民,趋之若鹜”。总之,康乾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当时呈现出一派交往频繁,共同开发边疆的热潮。这种互相促进的经济联系和并肩生产劳动结成的深厚情谊,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得到了普遍种植和推广。这两种作物都是从外国引进的,适应能力强,产量高,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江南地区大面积推广双季稻的种植,使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前,江南地区只有一次秋收,康熙末年,通过种植双季稻,变为两季成熟。
单季稻在丰收之年每亩最多收获三石到四石,双季稻两次收获,每亩总产一般均可达到六七石。其次,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作物,有了更大面积的种植,主要是大规模地种植棉花。长江三角洲、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有的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多,粮食种植相对减少,一度引起清政府的恐慌。除了棉花,经济作物还有桑、甘蔗、烟草、茶、兰靛、中药材等。由于追求高产,谋求厚利,此时的生产经营者已经不再光靠节约成本了,而是在劳动组织、生产安排、经营管理等环节上都进行考虑。这种生产管理思想的转变,与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有密切的关系。
手工业的进步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逐步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
顺治二年(1645年)一度宣布取消匠籍并免征代役银,表明国家对手工业工匠的控制和束缚有了前所未有的减轻。但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全国即将统一,企图恢复“班匠银”,明谕“京班匠价,仍照旧额征解”。但全国各地多是匠户逃散,籍名空寄,无法征收。康熙二年(1664年)下令将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征收,自此以后,各地陆续将“班匠银”摊入地赋中征收,匠籍也就随之逐渐的废除。废除匠籍表明手工业者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匠籍废除后,官府以“当官”或称“应官”为名,对工匠铺户进行科派的现象仍很严重。雍正二年(1724年)废除工匠当官差的制度,乾隆年间,又多次重申这一禁令。废除“匠籍”、禁止“当官”之后,官府役使工匠,普遍地采取雇募的办法,这种办法的实施,是有利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的。
清朝时的税收在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城市工商业者不再有丁银的负担,这也鼓励了手工业的发展。
乾隆年间,在一般手工作坊内为坊主工作的雇工,很多都和主人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这些现象也标志着清朝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有一定的提高。
清统治者为了鼓励手工业发展,放宽了民营的范围,除军器铸钱官营及景德镇、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少数瓷窑丝织手工工场官营外,都允许民营。例如:开矿,清政府本来一直严行禁止,其原因在于害怕“聚众生事”。康熙十四年(1675年)曾一度放宽矿禁,但只限于恢复旧矿。其后,逐渐允许民间开采铜、铁矿,把冶铜和煮盐都改为私营或官督商办。铜矿控制较大,生产物的一部分作为矿税上缴,另一部分必须由官府用低价收买,严禁私销。原来规定私人织机不得超过一百张的禁令,后来也取消了。这都说明清朝时民间手工业的种种限制已有相对的放宽。这些措施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手工业者对国家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是清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行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棉花原料的收购和纱布产品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数百家,工匠多至一万余人。
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天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政府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铁、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5000余人。
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政府对采矿的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
2-4清代手工业品
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此外,熬盐、伐木、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清代手工业很繁荣,无论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细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商业的繁荣
清朝时期,商业贸易较明朝有了更大的发展。
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更有了显著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盛,有些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和汉口,较明代更加发展。长江沿岸的无锡是著名的“布码头”,汉口是“船码头”,镇江是“银码头”。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货荟萃,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有景泰蓝、雕漆、玉器等,前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础上,屡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园林区,有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宫殿坛庙、街道河流亦经大力修建,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扬州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财贸殷富,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产品远销各地,城内商铺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农桑鱼米之利;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苏州有园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的窗口。
2-5清朝时期的商业
商业发展使白银成为主要流通手段,铜钱只起辅助货币的作用。大商人都拥有数十万两或数百万两的资金。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晋商、两淮盐商和广东的十三行。这些商人具有官商的性质。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十三行是经办对外贸易的商人团体,他们对官府的依附性也很大。虽然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程度不同地发挥过作用,但由于对封建肌体的寄生性,在分解封建生产方式方面并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虽然商业在清朝有所发展,但是,清政府把工商视为末业,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政府插手干预,指定官商,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且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手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会组织,这些都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