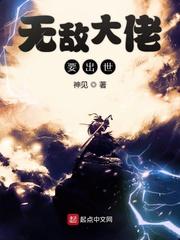456小说网>时光的印记作文500字左右 > 二 时光印记(第4页)
二 时光印记(第4页)
工厂班车是工厂为职工进城办事开设的,也是这个三线工厂为职工办的一件好事。在工厂与火车站之间二十公里的路上按点出发,来回穿梭着。
星期天的班车上吵吵闹闹,挤满了似曾相识的工厂职工。说熟悉吧,叫不上名字;说不熟悉吧,看着面熟。工厂的职工们大多属于上班打卡一族,只有星期天的时间才属于自己,才可以进城办点自己的事情,所以,工厂班车周末一向人很多。
这天的班车一停靠下来,门一打开,呼啦啦拥上来了七八个人,售票员被拥挤的人群堵在了后面,动不了半步。
她扯着嗓门喊着,门口上来的买票,买票,还没有买票的买票!喊声从众人的头顶传至整个车厢。
门口挤上来的几个人,翻着口袋,找出零钱递给了车厢后面的售票员。
还有谁没有买票?明明看见是八个人上来的嘛!售票员是位责任心很强的人,她一边翻着手里的钱一边喊道。
我有月票,门口传来一男子的声音。
什么月票,厂里就没有办过月票。
车厢里突然静了下来。
你站起来,让售票员看看你。旁边的人怂恿着没买票的那位。
没买票的人被身旁的几个人推挤到车门口高一级的台阶上,他伸着脖子,朝售票员望去。售票员看了一眼他,脸一红,收回了手里的票夹。原来,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通用的月票。
满车厢的人哄笑起来,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书梦
很小的时候,我就做着书的梦,梦的内容是希望自己拥有几本书看看。那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买书,有时碰上特别好看的书便爱不释手,但只能挑最精彩的段落、句子抄下,以至于到现在买得起书了,看书时也不忘做点笔记。
记得刚上小学,我便认识了不少字,成天找书看,从小人书逐渐过渡到长篇小说。那时候,农村的书很少,我便常在同学家里搜罗一些,诸如《我的一家人》《遍地黄花分外香》等,看完一本又一本,简直像着了迷一样。只要一有书,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直到看完方肯罢休。记得有一次母亲蒸馒头,让我拉风箱烧火。我边看书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拉着风箱,到头来,一本书看完了,一锅馒头也全烧黄了。
再大点的时候,仍做着书的梦。梦的内容是自己也要写书。看着一本本内容丰富的书,读着书里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下决心也要写写人生的乐趣、人生的疾苦,因此,我迷上了写作。从中学到大学,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还时不时发表,虽然那时还没有出一本书,可写书的决心却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走上社会后,书的梦变得时淡时浓。我仿佛才明白一本书的问世要经历多少努力、多少辛苦、多少生活的体验,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书。因此,每当那种“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感觉悄悄地涌来,我就会拿起笔,随便写些东西,但这已不单是为了发表作品和出书,而是为了给自己看,与自己的灵魂、与整个社会对话。心里淡泊了许多,情思反而涌来,我才懂得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书,一天又一天地翻着新页,写好人生的书才是非常重要的。
写书难,出书难,书梦却依然……路在我脚下延伸
下午突击写完作业,闲得没事,想起好久没有去楼那边的草坪上转转了,便放下书,信步走出教室。
沿着草坪上窄窄的小路走了一阵,觉得有些厌倦,近来常常这样,脑子里亦空空如也。偶尔回头一看,雨后潮湿的小路上,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这就是我的脚印?我的眼睛似乎潮湿了,路变得模糊起来……路的尽头,跑来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她迎着朝阳,欢快地走在上学的路上,那就是少年的我。当一个小班长,喜欢读《雷锋的故事》,幻想着当英雄,像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一样。那时的我很单纯。记得一次考试只得了八十分,我哭得连饭也吃不下。在那条上学的土路上,留下的脚印虽然幼稚但坚定有力。
我长大了,人们说我成熟了,我却感到失去了一种宝贵的东西。
上大学的第一节课,讲桌上蒙着厚厚的尘土,黑板涂抹得像一幅现代派绘画。老师走上了讲台,首先拿起板擦擦黑板。我环顾左右,那些人眼睛中没有羞愧和不安。我低下了头,假如在过去,我会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可现在……一边抱怨着老师留下的作业多,一边照着书上的公式做题。其余的时间呢?不知道都去哪里了。期末考试临近,便放弃一切活动,突击复习。只要能通过六十分“大关”,即意味着可以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什么理想和梦想,都与我绝缘了。静坐沉思时,心里也有一丝惭愧,但也是一晃而过。
我变了,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可我才十八岁,该怎样走完这漫长的人生之路呢?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在路上思考着,路在我脚下延伸……初次投稿
大四的时候,共青团陕西省委主办的《当代青年》杂志开设了一个大学生专栏,主要反映大学生的生活情况,专栏的编辑是南岭先生。我偷偷地将自认为不错的几篇散文和诗歌装进信封,在封面上工工整整、端端正正地写上收件人南岭的大名,寄了出去。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南岭是男是女,年方几何。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课间的时候,生活员递给我一个印有《当代青年》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想到自己曾经给《当代青年》投过稿件,便不敢当众拆信,恐怕别人看到了退稿信后自己难堪。等到下了课教室只有我一个人时,我才小心地拆开信封,发现信封里装的并不是退稿信,但也不是录用通知单,而是一个便笺。便笺上短短地写着几句话,意思是看到了稿件,印象不错,但跟杂志的风格有差距,希望来编辑部面谈修改意见。落款是南岭。看到这短短的几句话,我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毕竟,这是我第一次鼓足勇气向社会刊物投稿,虽然我之前在校刊上、报栏里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还没有在正儿八经的社会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过了两天,我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找到了位于红缨路的《当代青年》编辑部,不料南岭先生不在编辑部。当班的编辑告诉了我们他家的地址,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了他家。一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正是我们要找的编辑南岭先生。
那一天,他给我们讲了《当代青年》的用稿特点,并且讲了我那几篇纯文学稿件,虽然不乏文采,但离现实生活远了点,他告诉我投稿要分析每个刊物及报纸的用稿特点,有针对性地投稿。说完了稿件,南岭先生问了我们在大学的生活情况。当时正值毕业分配前夕,大家的去向一片渺茫,因此,我们言语之中不免流露出了忧郁担心的情绪。
回校后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南岭先生的一封信,长长的三页,信中以长辈的口吻给我叙说了他们大学毕业分配时的情况,以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分析了社会上报纸刊物的大众需求,鼓励我从精神象牙塔走出来,少一点书生气,勇敢地认识社会、面对生活。信的最后说,拟采用我的一篇散文,但题目不行,得换一个通俗易懂的标题。
这是一个老编辑给初次投稿的、只有一面之缘的我写的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对当时就要走出校门、走上社会的我来说,犹如一股清流,缓缓地流入我的心田,驱散了我毕业前夕紧张焦虑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