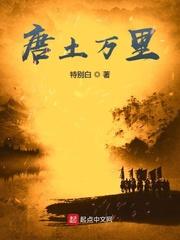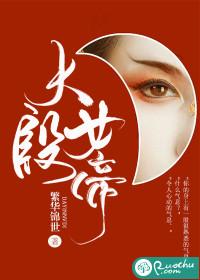456小说网>变身软妹 > 第194章 总结大会(第1页)
第194章 总结大会(第1页)
像是李大山这个篝火发生的场景,其实也在其他篝火的小团体里同时上演。
这原本就是饺子坡生产队高层决定了、甚至已经在实行的政策新规,只是还差最后的完善阶段,一直没有公布而已,如今工人们自发宣传,其实也正合他们的意,自然不会阻止。
这样子的议论反倒有利于激发工人们的工作热情,为了一份前程工人们也会老实许多,更便于管理。
因为入队的时间不同,同一批登记入队的人更容易分配到同一个帐篷、同一个小队。
当然,吃饭的时候不一定要在篝火处,但生产队里可不比灯火通明的京城商业街,距离那一团团篝火远一点都只能摸黑吃饭。
同小队的熟人间凑一起吃饭是常态。
一起吃一起住,自然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圈子。
从难民转化为工人,似乎只需要在登记册上写上名字,领到黄帽子后往头上一带。
惠娘亦是如此。
转眼间她已经进入这饺子坡生产大队十多天,在这里管吃管住,吃的住的甚至比他们逃荒之前的那个小村庄还好。
她无比庆幸那天与梁锦生划清界限的决定。
要不然她和身旁四岁的儿子都得面临一起被赶走,继续上山找啃树根的局面。
身旁同小队的姐妹们也在讨论着最新听来的小道消息,只是惠娘双眼盯着那闪烁的火光,手里机械地扒着饭,有些心不在焉。
其实饺子坡生产队里女人并不多,孩子更少。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里的工人全部都是出身难民,甚至大多数都是周边省份逃荒来的,路上不但有饥饿与寒冷,还有反贼劫匪,野菜挖不到的时候,连山上的树根都得抢。
体乏力弱的老弱妇孺大多都死在了路上。
有命活下来的,大多都是青壮男人。
所以在这饺子坡生产队上,虽然也有不少女人孩子,但男女比例相差还是悬殊。
为了照顾她们,也为了合理分配劳动力,饺子坡生产队的领导们专门给这些女人分配了饭堂的工作。
没办法,虽然饭堂里一些工作也需要力气,但和工地上伐木搬砖相比,让这些女人去当厨娘干一些后勤杂活已经是照顾了。
而且这些女人也是逃荒来的,可比不得城里那些个娇气小姐,干点粗活也是手拿把掐。
每天晚上的篝火晚饭时间是她们最舒服的时间,一天的工作干完,劳累的身体终于能歇下来,温暖的篝火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那是一种心灵上到身体上的放松。
所以她们之间谈话的语气也非常放松。
此时,篝火旁一起吃饭的小姐妹们在谈论的话题,正是关乎她们未来的“大事”。
“诶,都听说了吗?”坐在首位穿着黑色布衣的女子突然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