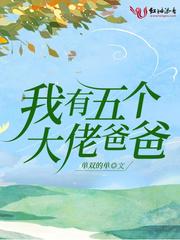456小说网>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 第1章 天文历法(第3页)
第1章 天文历法(第3页)
隋炀帝即位,刘焯被重新启用,任太学博士。当时,历法多存谬误,刘焯多次建议修改。00年,他呕心沥血造出了《皇极历》,很可惜未被采用。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达到很高水平。唐初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出的《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刘焯在科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
一、在《皇极历》中,他首次考虑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主张改革推算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废除传统的平气,使用他创立的定气法。这些主张,直到年才被清朝颁行的《时宪历》采用,从而完成了我国历法上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
二、刘焯力主实测地球子午线。源起是我国史书记载说,南北相距千里的两个点,在夏至的正午分别立一八尺长的测杆,它的影子相差一寸,即“千里影差一寸”说。刘焯第一个对此谬论提出异议。后于7年,唐代张遂等才实现了刘焯的遗愿,并证实了刘焯立论的正确性。
三、他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岁差(假定太阳视运动的出发点是春分点,一年后太阳并不能回到原来的春分点,而是差一小段距离,春分点遂渐西移的现象叫岁差),定出了春分点每7年在黄道上西移度。而此前晋代天文学虞喜算出的是0年差度,与实际的7年又8个月差度相比,刘焯的计算要精确的多。唐、宋时期,大都沿用刘焯的数值。
一行(7~77),本名张遂,河北巨鹿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
一行自幼聪颖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去元都观拜见博学多闻的道士尹崇,尹崇借了一部西汉扬雄所作的《太玄经》给他看。《太玄经》是一部文词艰涩、内容隐晦的书,一般人很难看得懂。隔了几天,一行便把这部书交还尹崇。尹崇以为一行是觉得这部书实在太玄了,看不懂,所以就赶快还书。但当一行拿出他的读书笔记请教尹崇时,尹崇惊讶不已,他对一行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并向外宣扬一行的学问,从此一行就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于长安。
唐玄宗时,一行受命编写新的历法。他准备开始观测天象的时候,发觉当时所用的天文仪器都已经陈旧腐蚀,不堪使用。他便立刻重新设计,制造了大批天文仪器,还在世界上第一次组织了大规模的子午线长度测量工作。
制造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
在修订历法的实践中,为了测量日、月、星辰在其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其运动规律,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浑天铜仪是在汉代张衡的“浑天仪”的基础上制造的,上面画着星宿,仪器用水力运转,每昼夜运转一周,与天象相符。还装了两个木人,一个每刻敲鼓,一个每辰敲钟,其精密程度超过了张衡的“浑天仪”。“黄道游仪”的用处,是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的座标位置。一行使用这两个仪器,有效地进行了对天文学的研究。
测量子午线
7年(开元十二年),一行修改旧历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许多,于是开始着手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一行的测量工作以河南为中心,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以南,广泛收集数据,以求测出当地北极星的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时日影的长度。河南周边的那些测量点,由太史监南宫说带队测量,测量的重点是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处的数据。
这次测量跨度大,时间长,一直到两年之后,各种测量数据才陆续汇集齐。一行和南宫说立即投入了复杂的计算。他们终于算出了:北极星高度相差一度,南北间的距离就相差里80步,折合成现在的距离就是9。千米,这正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一行测量子午线,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为后来的实地测量和天文学奠定了基础。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史研究者都认为,这确实是一次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活动,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制定《大衍历》
7年(开元十三年),一行开始编历。经过两年时间,写成草稿,定名为《大衍历》。《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最突出的表现是它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与变化规律。自汉代以来,历代天文学家都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行采用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推算出每两个节气之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距却不同。这种算法基本符合天文实际,在天文学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仅如此,一行还应用内插法中三次差来计算月行去支黄道的度数,还提出了月行黄道一周并不返回原处,要比原处退回一度多的科学结论。《大衍历》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明末的天文学家们都采用这种计算方法,并取得了好的效果。
《开元占经》全名是《大唐开元占经》,作者是瞿昙悉达,成书时间约在718至7年之间。唐朝以后,《开元占经》一度失传,所幸在明末又被人发现,才得以流传。全书共0卷,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和纬书,还介绍了种历法有关纪年、章率等基本数据。在书中,各种物异和天文星象等方面的术语很多。
瞿昙悉达祖籍印度,其先世由印度迁居中国。关于他本人的生平史料传世很少。在《开元占经》卷一中记载,唐睿宗景云二年(7年),瞿昙悉达奉敕作为主持人,参加修复北魏晁崇所造铁浑仪的工作,并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年)完成。在《旧唐书·天文志》中又记载有,瞿昙悉达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8年)奉敕翻译印度历法《九执历》。这部历法后来被录入了《开元占经》,至于瞿昙悉达何时编撰《开元占经》,史无明文。但据今人薄树人考证,瞿昙悉达大概在开元二年(7年)二月之后奉敕编撰《开元占经》的,至于编成时间,则应在开元十二年(7年)前后。
《开元占经》中关于日蚀现象的论述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当时已发明了预报日食的方法,但在时刻计算上还比较粗疏:天文学家借助了一盆水使观测者专注的目光从长时间向上仰视刺目的太阳光本身转变为自然微俯观测刺目程度较低的水中太阳像,从而可以大大减轻观测者的痛苦和疲劳。这个观测方法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观测日食的能力和质量。此外,《开元占经》还集录了日全食时人们看到的太阳外层的一些现象,如日珥和日冕。
另外,《开元占经》记述了大量古代天文学家有关宇宙结构和运动的认识,而且其中有一些是仅见于此书的。如后秦天文学家姜岌的《浑天论参难》,梁武帝在长春殿召集群臣讨论天文、星象的记载,以及祖暅对姜岌的批评等等。还有些论述在别的古书中虽也有所记载,但是《开元占经》所录却更为详尽。如对祖暅的《浑天论》、陆绩的《浑天象说》等的记载都较《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所记为详。所以,集中记述宇宙理论的《开元占经》卷一、卷二,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必读之书。
《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大量已失传的古代文献资料。据初步统计,《开元占经》中摘录有现已失传的古代天文学和星占学著作共约77种,纬书共约8种。这些佚书在其他古籍中间或已有记载,但完全不如《开元占经》丰富。如有关纬书,明代曾有一位学者孙珏从许多唐宋古籍中辑录出一部纬书辑佚集,题为《古微书》。然而,自《开元占经》重新发现后,清朝人所辑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所辑纬书篇幅超出了《古微书》好几倍。至于天文学和星占学的著作,则还没有人全面重新辑佚过。此外,《开元占经》中还摘有若干现已佚失的经学、史学和兵家著作。总之,《开元占经》作为保存古代文献的著作来说,称得上是一座宝库。
苏颂(00~0),字子容,厦门同安人,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
苏颂出生在一个书香仕宦之家,他的祖父、伯父、堂叔、兄长都是宋朝的进士,他的父亲苏绅担任过大理寺丞、尚书员外郎、直史馆、翰林学士等官职。在如此的家庭环境下,苏颂自幼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岁那年便与王安石同榜考中进士。从那时开始,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最后位及宰相,为官50多年,政绩颇丰。
实际上,苏颂在处理宋朝政府事务时,已经显示出作为一个科学家严谨治学的行事风格。苏颂曾在宋朝的文史馆和集贤院任职九年。工作的便利,让他每天能接触到皇家收藏的许多重要典籍和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本。苏颂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每天背诵两千字文章,回家后再将它默写记录保存下来。经过长期的积累,苏颂的学识变得更加渊博。在这九年里,苏颂还与掌禹锡、林亿等编辑补注了《惠佑补注神农本草》,校正出版了《急备千金方》等书。又主持编著了《本草图经》卷。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对《本草图经》的科学价值亦予以极高的评价。
苏颂一生标志性的贡献,在于他制成了水运仪象台。08年(元丰八年),苏颂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天文、数学、机械学知识开始设计制作水运仪象台,历时年终于告成。仪象台以水力运转,集天象观察、演示和报时三种功能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其后,苏颂又写了《新仪象法要》卷,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及使用方法。
根据《新仪象法要》记载,水运仪象台是一座底为正方形、下宽上窄略有收分的木结构建筑,高大约有十二米,底宽大约有七米,共分为三层。上层是一个露天的平台,设有浑仪一座,用龙柱支持,下面有水槽以定水平。浑仪上面覆盖有遮蔽日晒雨淋的木板屋顶,为了便于观测,屋顶可以随意开闭,构思比较巧妙。露台到仪象台的台基有七米多高。中层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里面放置浑象。天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之下,另一半露在“地平”的上面,靠机轮带动旋转,一昼夜转动一圈,真实地再现了星辰的起落等天象的变化。下层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等。设有向南打开的大门,门里装置有五层木阁,木阁后面是机械传动系统。
水运仪象台的构思广泛吸收了以前各家仪器的优点,尤其是吸取了北宋初年天文学家张思训所改进的自动报时装置的长处;在机械结构方面,采用了民间使用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机械原理,把观测、演示和报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一部自动化的天文台。
因此,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认为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甚至是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沈括(0~09),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和出色的外交家。
沈括小时候有一个爱刨根问底的习惯,喜欢琢磨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问题。有一天,沈括正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背诵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突然,一阵风吹来,将院中树上的桃花吹落在地。他想: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已经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白居易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还号称大诗人呢?
母亲为了让沈括弄清楚这个问题,特意让他邀请几个同伴一起到山上散散心。沈括他们来到山上,果然满山的桃花正在怒放,这可把小沈括难住了。同样是桃花,为什么这里的却开得这么晚呢?突然,一阵冷风吹来,他顿时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脑门大声说:“我明白了!原来是山上地势高,温度低,所以花开得就晚,这是由气候条件决定的!”
小沈括回到家后,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记录下来。从此,沈括对气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有关气象的书籍,注意气象的变化,立志要做一名气象学家。
中国古代一贯是阴阳历并用的,因此历法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阴阳历之间的调合问题。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的运转周期为9。088天,地球绕太阳的动转周期则为。天,这两个数互除不尽。这样,以十二个月来配合二十四节气的阴阳合历就始终存在矛盾。虽然我们祖先很早就采用了闰月的办法来进行调整,但是历日与节气脱节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括进行了长期周密细致的研究。他说,寒去暑来,万物生长衰亡的变化,主要是按照二十四节气进行的,而月亮的圆缺与一年农事的好坏并没有很大关系。以往的历法仅仅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定月份,节气反而降到了次要地位,这是不应该的。正是从以上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革的方案:以纯阳历取代阴阳合历,这就是十二气历。沈括指出,只有纯阳历才能把节气固定下来,从而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对历法的需要。
十二气历是完全按节气来定历的历法制度。它把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分为孟、仲、季三个月,以立春那天为孟春之月的首日,以下类推,用节气来定月份。每月有大有小,大月日,小月0日,一般大小月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即使有“两小相并”的情况,也不过一年中出现一次。有“两小相并”的年份为天,没有的年份为天。至于月亮的圆缺,虽与节气无关,但为着某些需要,可在历书上注明“朔”、“望”。这是一种纯太阳历的历法制度,既与实际星象和季节相合,又便于各种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