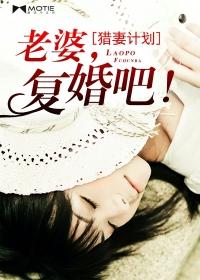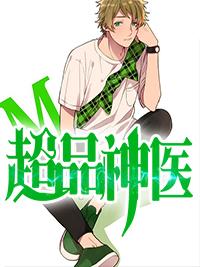456小说网>别轻易相信任何人英语 > 第六章 谨慎是预防被骗的万应灵药(第2页)
第六章 谨慎是预防被骗的万应灵药(第2页)
老沈看这个中年妇女满脸汗水,眼圈发红,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而且一边跟他说明情况,一边接听电话和打电话,询问家人走到哪里了。老沈平时就是个热心肠,见这个女子这样焦急地求助,连忙站起来关了电视机,帮她去联系殡葬服务公司。
老沈在这家物业公司做看好几年保安,对小区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他知道,12楼确实有个姓刘的老人是病入膏肓的阶段,女儿每天来看他,都要从保安的岗亭旁经过。如果老人真去世了,那自己确实应该帮帮这家人。他想,这个儿媳妇这么着急,而自己又是物业管理人员,出面帮忙协调一下是应该的。因此,他一边安慰该女子,一边打电话向物业经理陈女士汇报情况。在刘家儿媳的要求下,老沈还帮忙请了小区外面一家殡葬服务公司帮忙打理。
物业经理陈女士来到现场查看情况后,叮嘱道:“家属节哀!灵堂尽量搭在外面,晚上时间不宜过久。”经过一番提醒和安慰,陈女士也尽心尽力地帮刘家儿媳联系殡葬服务公司。
殡葬服务公司的员工报价,整个灵堂的搭建和其他杂务需要共计2。6万元,刘家儿媳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不久,殡葬服务公司来了十多个员工,把钢架、花圈、雨棚等都搬过来。刘家儿媳又到小区外面的餐馆订了几桌酒席,又到鲜花店预定了一些鲜花。
经过这一番折腾,本来安安静静的小区绿地上,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工人们手脚勤快地搭着灵堂,灵堂和冰棺很快就搭设好了。餐厅接到大订单,赶忙安排做饭菜。花店老板也再联系鲜花紧急配送。
这时,刘家媳妇面色焦急地找到老沈,对他说,自己把家里钥匙落在车上了,要等车到了之后,才能拿到现金和银行卡,又说自己还得买点花生、瓜子和其他用品,问老沈能不能借给她1000元钱,家人一到立刻就还给老沈。
老沈是热心肠,自然不会拒绝,随即拿了1000元钱借给刘家媳妇,连借条都没用她打。刘家媳妇拿着钱,又去看正在搭建的灵堂,见一个姓孟的写挽联的师傅,便跟他说,自己还差点钱,小区保安沈师傅已经借给她1000元了,问老孟能不能再借给她2000元。老孟兜里正好带了1500元,心想,既然小区保安都借钱给她,一定是平时很熟,也就没太多想,直接把1500元借给了她。
刘家媳妇一拿到钱,就跟大家说出去买花生、瓜子,让老沈帮忙照看一下灵堂,老沈满口答应。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家媳妇这一走,再也没回来过。本来她说好下午3点公公的遗体会被送到灵堂这边,可是4点已经过了,大家还是没等到有车来送遗体。
刘家媳妇也没了踪迹,大家这才怀疑可能有鬼,于是老孟跟老沈说:“赶紧上楼问问!”他们跑到楼上按12-3的门铃,里面出来一个老奶奶和一个中年妇女,并没见到刚才那个自称刘家儿媳的女子,老孟和老沈这才如梦初醒。
12-3的老奶奶对他们说,她老伴确实重病在身,但并没有去世,家里也没有儿媳。看见他们在楼下搭灵堂,女儿路过时还奇怪,到底谁家这么兴师动众呢?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利用他们家的病人去骗人,顿时觉得又气愤又晦气。
消息一公布,楼下几十人全都停下了手上的活儿,众人除了生气,就只能自认倒霉,纷纷撤离小区。老孟和老沈只好求助当地警方。
事后,老沈无奈地说,这个女的就是个十足的“影后。”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居然会用这种手段行骗。回想起那天的遭遇,他觉得十分气愤,连连苦笑。1000元虽然花不了一辈子,但自己只是一个低收入阶层的保安,这帮骗子居然能骗到自己头上,真是坏到骨子里去了。
警方接到报警后开始进行调查,并提醒众人,即使骗子设计的场景十分紧急,也不能被同情心蒙住了眼睛。如果有人求助,需要再三核实其身份,并留下联系方式,最好是两个人以上的电话等,以免被骗子得手。
设想一下,如果老沈懂得微表情和读心术的技巧,也许就会对他人多一层怀疑,少一点轻信。《别对我说谎》里的莱特曼博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通过测谎试验,断定路边卖小吃的人上完厕所没有洗手,便不吃他卖的东西了。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把微表情测谎技巧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每件小事上,那么轻信他人而上当受骗的事情一定会减少。
无论谎话说得有多圆,都一定会有漏洞,毕竟“真相只有一个”。在查明真相方面,微表情的作用功不可没。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克曼博士,是《别对我说谎》中莱特曼博士的原型,他对微表情的研究是以西方人惯用的“分解”手法为基础的。他把人类的肢体,特别是面部表情肌像拼图游戏一样分解开来,然后逐一分析它们的移动情况,据此推断拼图者的真实心理。因为表情比语言诚实得多,所以,在识别骗子的撒谎招数时,最重要的不是听语言,而是观察表情。
《别对我说谎》里的两位主角的扮演者,蒂姆·罗斯和莫妮卡都表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想像剧中的莱特曼博士和微表情识别天才托雷斯那样,每天审视和观察别人。他们宁愿过自己的生活,在拍戏之余少接触关于微表情的知识,以免让自己变得精疲力竭。
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微表情可以帮助人们识别谎言,防止被骗。因此说,老沈和老孟若能观察一下这个女子有没有单肩耸动、摸鼻子、脸部两侧表情不一致等情况,相信一定能观察出一些破绽。女骗子虽然演技高超,但也只是在普通人面前耍耍诡计,一旦遭遇“细心者”,她极可能原形毕露。
3。老专家的读心妙法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谎言是善意的,不但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还能起到息事宁人的效果。因此,微表情利用最多的领域还是在刑侦方面。这并不奇怪,因为只有刑事犯罪分子的谎言会才会对他人构成实质性的危害,所以,识别谎言成为刑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微表情这个有力武器来协助完成。
在这方面,国外专家虽然首开先河,走在了我们前面,但中国也不乏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闫明(化名)就是其中一位,他可能是犯罪分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人。这个身体情况不佳的老人,乍一看根本不符合人们对“神探”的定位。但是,他绵里藏针,侦破疑难案件比一般的刑侦人员要有办法得多。
他原是公安大学的教授,近几年才因病退休。跟其他教授不同的是,他工作的地方以肃穆的审讯室和血腥的凶杀现场居多。他是中国微表情界屈指可数的专家级人物,也经常被各地公安机关邀请去破案,作为侦破疑难案件的最后杀手锏。
他的侦探生涯仅持续了十几年,侦破的案件却高达一千多件,包括变态杀人案、灭门惨案等,甚至一些根本没有头绪的陈年老案,都在他的侦查下迎刃而解。
他否认自己是个测谎专家,因为测谎一般需要辨认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真还是假。而他面对的嫌疑人,有时候会一言不发。可是有微表情技巧做指引,他不需要嫌疑人开口,就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他的办案经验和理论基础是“心理痕迹”。也就是说,每个人做每件事情,都会在心里留下痕迹,只要捕捉到这些痕迹,案件就有望告破。这在理论上跟测谎是截然相反的,故此闫明把它称作“测真”。只要罪犯真做过,他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
闫明在国家恢复高考之后,考上了心理学专业,并师从中国心理学家赵铭奇(化名)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公安部直属的公安大学任教。
90年代初,中国公安系统已经引入了美国的测谎技术,利用的主要是美国人的“准绳法”,意思是对有关问题的关注程度可以用来区分无辜者和犯罪分子的心理。当一个犯人在接受心理测试时,虽然他外表可以装得很平静,但内心肯定是有波澜的。测谎仪就是测定这种波动的法宝。
可是在实际工作中,闫明发现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如果一个犯罪分子的心理素质极佳,而一个无辜的人心理素质又极差,误差就可能产生。
一位俄国心理学家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当他想象自己正在做刺激的过山车游戏时,心率会骤然上升到100次以上。而且通过生物反馈方面的训练,人可以达到控制自主生理反应的目的。如果遇到这样的刑事犯罪分子,“准绳法”可能就不管用了。
相反,一位美国教授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做过一个实验,把测试谎言变成测试记忆。这位学者认为,无辜者和罪犯心理上的差异在于,发生犯罪时,罪犯在现场知道的一切。他的记忆里保存着这些数据。可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记忆里是一片空白。
这种理论,即使在美国也不占据主导地位。可是闫明在实践基础上,提出如下观点:心理测试技术并不一定需要测定口供的真实与否,而需要测定罪犯有没有跟案情有关的心理痕迹。只要罪犯实施过犯罪,他头脑里就会留有心理痕迹。测谎仪对被试生理指标的追踪,依据的也是这一点。
一次,华北有一个棘手的案件请他协助办理。案情是这样的,有个村子的老太太死在家里,案发现场出现性虐和焚尸等迹象。闫明认为,这些特征都说明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变态杀人案。在闫明去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警方除了抓获一名嫌疑人之外,办案没有一点进展,大家都愁上眉梢,只好求助于闫明。
就这样,闫明来到华北,审问了嫌疑人之后,让公安局把他先放了,因为没有找到证据证明该人实施了犯罪。经过现场了解,闫明推断这个案子的罪犯就在这个村子里。罪犯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杀人后进行尸体性虐,说明该罪犯心理没有恐惧感,觉得很安全。而且作案后还进行焚尸,伪装现场,掩饰犯罪行径,说明此人离这里很近。因为如果离得远,焚尸灭迹就显得多余了。
另外,此人作案前肯定去过被害人家,对这个房子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包括对老太太单身居住的情况,等等。因此,流窜作案首先被闫明否决了。
划定了嫌犯范围之后,闫明让当地公安局把村里所有有前科的、离婚的、有变态倾向的、打光棍的、入过狱的都找来,划定了一些嫌疑人,也包括之前放走的那个。闫明采用心理痕迹法,对这些人逐一进行审讯,很快就把真正的元凶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