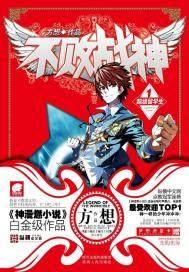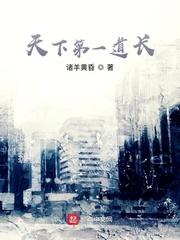456小说网>曾国藩对胡雪岩评价 > 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第3页)
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第3页)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际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际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人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知一句便行一句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详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日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日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日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日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日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土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来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曾国藩越到晚年,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铁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尚虚名,贵求实效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
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王阳明说”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对孟子观点继承并加以发扬,“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工夫好名?”古人重实轻名,并非纯从道德上讲,而是看到了重实的益处与好名的危害。先贤把务实看成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于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苟悦认为,务实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说:“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则会引来灾祸。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名心盛者必作伪。”揭示了好名者的实质。《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三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称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所以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让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之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要使自己重实轻名,并非一件容易事,这就看个人的修养高低了。曾国藩受理学的薰陶,受实学浸染,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他于1851年便在日记中记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名。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留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则是最大的灾难。曾国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因此应脚踏实地做事,不要贪图虚名,因为“虚名不可恃”。他对兄弟们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而聚然得名主人,“其为名必过情”,要想不过情,就要像四时那样运作,使人不觉,而事业已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味回护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名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功名官爵,不能过分贪恋,应当急流勇退,避免杀身之祸。历史上,范蠡和张良是做得最成功的两个人。他们成就大业后,并未贪恋功名,及早退身避祸,传为美谈。曾国藩也深信此道。他没有像范、张二位退身归隐,却也达到了同样目的。他从不接受有名无实的虚名,他任两江总督时,虚衔多达几十个,一枚印章都刻不下,曾国藩只选了其中较重要的几个刻成印章。对于有些虚衔,曾国藩干脆奉还给朝廷。这样,他的名总是与实际相符,而且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清廷也便不会对他下手。所以曾国藩能常保不败,在风云变化不测的官场履险如夷,可说是得“实”字诀之力。
“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间津。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