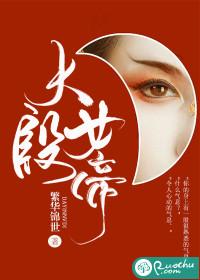456小说网>胡雪岩与曾国藩的智慧 > 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第2页)
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第2页)
曾国藩淡薄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
曾国藩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他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
因此,他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要做到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是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他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就会直接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他主张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所谓“改过”,曾国藩指出,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每天认真检讨所作所为。对于友人的忠告,他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他的铭联、箴言、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
无贪无竞,省事清心,十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治心经”是他的独特心得,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他强调养心,认为养心可以达到养身的目的。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他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囱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基于这种看法,他对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最为赞赏,他说,在官场中混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的“规矩”: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要保持一团和气;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苏轼认为,人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因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并战胜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苏轼的处世之道十分推崇,他把苏东坡所作的能与他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留意养身之道。论及养身之道,曾国藩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宇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祖父“不信医药”的训导。
曾国藩养心的方法,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做“心理的修养”,他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他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他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做“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对于养生的道理,他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词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对于养生的项目,曾国藩还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对于养生的方法,曾国藩强调以静养为主,他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
‘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工夫,有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曾国藩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对于节制恼怒,他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褊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起居饮食有规律,爱好运动,节制少怒,都与现代的健康学非常相符合。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合雄奇于淡远之中
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其实,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曾国藩也是追求一种淡远之境的。
曾国藩虽事务繁忙,却从不忘忙中取乐。写诗、作文、下棋就是他的求乐养心之法。曾国藩每晚都在室中朗诵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文,自称得其中淡远闲适之乐。他经常临摩名家书法,刘墉(文清)是他最佩服的书法家之一,原因在于刘墉笔意;中淡闲远,最适于修身养性。
在欣赏古诗文淡远意境的同时,曾国藩不忘与自己急于名利之心作对比,以此来警惕自己。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热极,因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东花满溪”诗,念古人胸次萧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又何小也!
一方面欣赏古人的磊落胸怀,一方面又想在诗文方面胜过古人,急于名利之心在写诗作文上都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宽心、要淡然:
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己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除了研究古代志趣高远、才情并茂的诗人外,曾国藩还非常注意教导自己的后辈,从诗文入手,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以逞自己平生未尽之心。同治元年(1862)七月,他教导儿子曾纪泽说: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份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诀的妙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