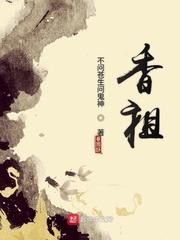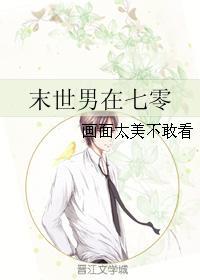456小说网>当官必读曾国藩 > 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第2页)
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第2页)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前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即用他的长处,同时与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把事业交给光大门庭之人
曾国藩做人有自己的要诀,这个要诀即做人心法。他不但有事业,而且找到事业上的继承人,把这种事业推进下去,把门庭继承光大下去。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他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自己有同年之谊,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是同僚,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又何以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巨舰,不是我这里的瀑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此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时也不例外,而且他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都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曾国藩、李鸿章,一个湘人,一个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剧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打鼓。从此,他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老师,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