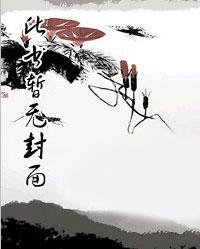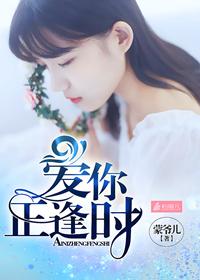456小说网>傀儡免费阅读 > 第55章 蚝油与炒菜(第1页)
第55章 蚝油与炒菜(第1页)
养殖海货如种田,这个概念几乎一语惊醒梦中人。
左仁绍几乎立时喜形于色,左氏有钱,而且非常有钱。也正因为站队早,左氏并未遭遇什么搜查,只是自行分个家便罢了,左氏家中钱财并未受到影响。
因此,这段时间以来,左仁绍最头疼的事,就是如何将左氏从盐业中给“拔出来”——田地倒是能买,也能雇人种,只是田产出息毕竟有限,何况分田的政令一下,雇人都不好雇了,终归不是个好法子。
是以陈泽提出这个海产养殖的概念,又讲解了一番之后,左仁绍实在心动。
于是,他甚至顾不得谨慎,一连问了许多细节。
陈泽也跟着一一介绍,不独海产,什么淡水养殖、珍珠养殖等等,都提了一些。
那么多可做的产业,他自己肯定来不及挨个去试错,还不如干脆洒给这些地方大户,让他们尝试,既能转移风险,也能带动地方经济。
自然,更重要的是,将来税制改革以后,商税可不会少收,这些大户赚的越多,陈泽收税也就收得越多,他当然对地方经济繁荣发展乐见其成。
等两人讲的口干舌燥,陈泽方呷了口茶,对身旁的计都叮嘱道:“小计,你把这些都大概记一记,回头咱们抽空梳理一下。”
“哎!”
计都当即应了声,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和一只纸卷炭笔,唰唰唰地写了起来。
细细算来,这还是陈泽带起来的风气,现下他身边的几个识字的亲卫,和府衙中不少吏员都有了这个习惯:将纸裁成巴掌大,然后一页页用线缝起来,再随身带一只用纸卷起来的碳条,制成简易的炭笔和笔记本。若是有临时需要记下来的东西,随手掏出来就能记,待有空之后,再整理册子上的笔记,总比自己用脑子记要方便不少。
唯一不好的就是那碳条太容易糊,是以小册子只能记单页,若是两页都记,要不了多久,字迹就会糊成一片,难以分辨。
陈泽熟练地说道:“主要记一下对孤竹县的规划,除了制盐厂,还考虑海产养殖业,这个就是咱们上谷郡的‘菜篮子工程’之一,要丰富百姓的餐桌,除了保证盐价要低,还要保证隔三差五能吃上荤腥,海货、鱼、虾等等,鸡、鸭、猪的养殖场也可以考虑……不过后者在哪里都行,回头咱们得先在郡城落实一下,先让御临卫和吏员们的餐桌丰富起来……”
絮絮叨叨了好一会儿,计都的小册子都写了好几页纸,陈泽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
韩三等人早就习惯了陈泽的行为,倒是左仁绍,看得是大为震惊。
古往今来,不是没有为民请命的人,也不是没有关心百姓的官员,可他们都不似陈泽这般,就好像……就好像要把每户百姓都要照顾起来似的……
不,应该说,就好像他将所有百姓都当成了责任,也都看成了人。
“左大爷!太守!”
就在室内一片安静,只听计都手中炭笔摩擦纸面的唰唰声时,福来饭庄的掌柜点头哈腰地拐进屏风,赔笑道:“小的是来禀报一声,老父母使俺们煮的海蛎子已经收了汁儿了!”
陈泽一听,顿时从椅子上起了身,顾不得掌柜那声令人哭笑不得的“老父母”,当即招呼众人道::“赶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