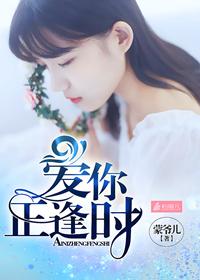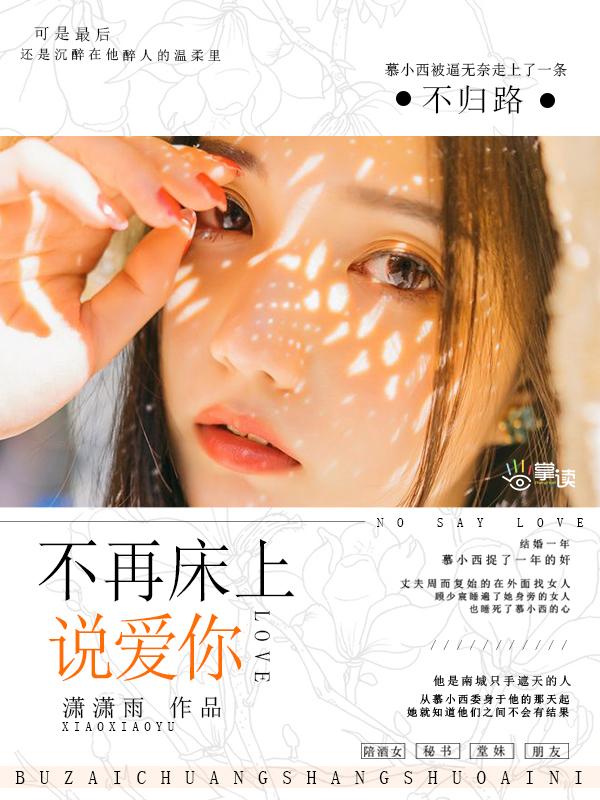456小说网>初世是什么意思 > 02(第3页)
02(第3页)
关于崖塌,西崖仅个别小局部有所发生,如74窟以西下层52—56窟附近及其上部,破坏甚微。严重崩塌在东崖和中部。庞大的崖体冠部下压产生的切力和应力,又上部大型开凿(如4、5窟)改变了结构和平衡,由地震引发了大面积崩塌。中部应发生在第5窟牛儿堂造成后不久。第4—5窟间及以下,山崖的折角突起以西,从东上斜向西下,崩塌面呈平行四边形,约横26、竖27米。据其两侧波及洞窟之受损程度推测,东侧自上而下,如14、15、16、17、19、20、22、23、24、26、27、36、37、39、40、43、49等窟,塌落崖面厚度约1~1。5米至0。6~0。8米不等,总体是上部崖体厚而下部薄。西侧由上而下如143、144、148、165、74、78、80号窟,所塌岩厚约1。8~1。5米至1。2~0。8米,也是上厚下薄。由此推断,其中心部位塌落崖体约厚1~2米间,所塌窟龛多属小型者。无74、78一类深3米左右的大龛。此类方圆敞口大龛,正是学界公认麦积崖的最早窟型。所以,在初期崖面尚且充裕时,最早开凿的佛龛不会选择那种危险地带。退一步说,即使该区域曾开凿最早的窟像,也不大可能全部都在这里而崩塌无存吧?因此,我冒昧建议放弃麦积崖创建洞窟已崩塌不存的观念。这其实是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又等于是个“死结”。它似乎延迟了对云冈、麦积之间异同及其原因的认真思考。
2.麦积78窟火烧迹象的解释
该窟佛座的坛基叠涩上,包砌掩盖一些木框被火焚烧,其制作相当规整。这是佛坛外表镶嵌的边棱?还是坛内木骨架?应藉适当时机分析或解剖清楚。张学荣先生曾指点我目睹过,印象属于前者,坛基的叠涩似以木框成型。原制作或裸露,表面髹漆,比草泥、土坯砌筑的边缘更美观实用。它可能是麦积崖造塑窟像的传统工艺。此木边框被焚当是洞窟失火所致,如木栈道、窟檐、门窗之类燃烧必将殃及窟内。据张学荣氏及夏朗云的披露,除78窟,其他74、57、90、165及80、100、128、14、148等窟,也有被火焚烧和重修的同样情形,[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栈道火焚情形,见张学荣《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又夏朗云《麦积山早期大龛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而在它们周围的其他窟龛中却不曾发生。这足以断定它们曾共同遭遇过一次焚烧的破坏—即北魏太武帝灭法行动。而坛基上的修复痕迹,包括用墁泥遮盖这些火焚木件,特别是仇池镇供养人画像、榜题无烟熏火烧迹,佐证供养画像为重修重妆,在火焚之后,晚于开窟造像。所以,步连生、张学荣二家关于窟像、供养人画像二者关系的解释判断无隙可击,是正确的。[见步连生《麦积山石窟塑像源流辨析》,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学荣、何静珍《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文物》1983年第6期;《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
又74、78窟现佛像为“文成复法”后新作之说,亦需审视推敲。一是此说全凭推理,并无实据,据张学荣氏介绍,麦积崖太武灭佛的破坏实际上不甚严重。[据张学荣《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文物》1983年第6期,麦积崖一、二期洞窟57、74、78、80、100、128、148窟等,都曾被火焚烧,塑像、壁画皆经重修,方式方法相同,重修程度轻微,都仍保留原作风格。从而判断太武帝灭法时曾有轻度破坏,文成帝复法后加粧重修。]而距离再远一点的河州炳灵寺,据169、1、16号窟的观察,看不出太武灭佛时有何破坏。建弘元年(420)所作无量寿一舖像,包括彩绘等依然完好。其次,灭佛时即使“焚烧击破”,按佛家仪轨习惯,也是原物装藏,原胎重妆,一般并无弃旧造新之理。上述74、78诸窟,造像皆系原作,像窟一体。如属重修而改变原貌,还是容易分辨识别的。也一定会留下痕迹,如165窟即是。
比较与分析
按麦积早期、云冈一期之孰早孰晚,分歧起于对二者和早期石窟作品之关系未作深入研究,而关键又在于如何认识,今试作对比剖析。
一、造窟之题材和形制
云冈一期即昙曜五窟的16~20号窟。关于麦积崖,我曾指出其最早的“(一)类”即一期佛龛包括:51、74、78、90、165、70、71、73、68号,看来还需要增补57号即“湫洞”。[见初世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麦积崖57窟是自然渗水溶洞,洞内按74、78窟形制予以修凿改造。笔者调查时,该窟尚不能通达。]“(二)类”窟龛,有80、100、128、144、148、149、176等,开凿年代在74、78等窟之后,第(三)类即太和初、中年之前。二类或二期所指实际为北魏早期。年代在文成帝复法之前后。在我看来,二期的北魏早期与十六国晚期的后秦、西秦、北凉之间是难以截断的,已如前述。
关于麦积一期、云冈一期造像,是在《法华经》、《坐禅三昧经》等大乘三世、十方、弥勒的信仰、禅观指导下设计开凿的,学界已形成较一致的看法。邓健吾、久野美树先生已从佛经义理、禅观方法、布局型式的渊源上找到证据,甚具说服力。[见(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管秀芳、魏文斌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同时,三世佛也是贯穿麦积一期、云冈一期各自后续时代的主题。但北魏创建说由此推论麦积一期及以下的三世佛信仰皆承之于云冈一期,却缺乏任何具体的理由。
先看基本特征。
麦积一期的设计:
1.方圆敞口大龛,无前室(按龛口稍有崩塌)。三壁前连续高坛基,三壁三坐佛(过去、现在、将来)等大。正壁释迦牟尼如願印、胁侍二菩萨,两侧佛禅定印。背景上方左右二圆拱小龛代表兜率天宫的思惟、弥勒菩萨。(51、57、74、78、90窟);
2.同前形制无坛基,正壁单独的交脚弥勒主尊、二胁侍(?),无背景小龛(165);
3.敞口小窟龛,一释迦牟尼禅定印、高座,二胁侍菩萨(70、71、73、68)。
云冈一期的设计:
1.形制为草庐、穹庐式,设明窗、窟门的大窟;
2.三世佛皆一大(正壁主尊)二小,共三种布局:
三立佛,主尊有二胁侍菩萨,壁凿千佛及释迦多宝并坐龛(18);
主窟一大坐佛,二耳窟倚坐二小佛,壁凿千佛(19);
主尊禅定印坐佛,背后凿隧道,二小佛立两侧壁(20)。
以上三窟为一组,19窟最大居中,同时开凿。
3.主尊释迦立像与二胁侍菩萨一窟(16);
4.主尊交脚弥勒菩萨与二立佛一窟(17)。
以上二窟一组,同时建凿,完成于二期。
从形制观察,云冈窟形更像穹庐(帐幕),椭圆形平面,方门,天窗可采光通气。或像天穹,无台坛,席地而坐。总之,颇似鲜卑习俗,不可能是模仿印度草庐,造意也与龟兹前堂后室中塔柱大像之窟相去径庭。
麦积崖大龛,窟形方正,三壁、壁角、龛口皆向上作圆弧形,收拢为小穹庐顶(78窟最为明显),法“天圆地方”,似宇宙空间,与窟内圆拱小龛象征天上宫阙一致。这种形制,在国内再无同例。正如久野美树所指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的群佛和视野,是“须弥山”下禅修观佛三昧的绝妙境地。[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管秀芳、魏文斌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布置手法。其中,165窟又是74窟等窟内小龛的单独放大,造像内容全同。该窟位于78窟正上方距离甚近,或怀疑他与78窟为“双窟”关系。“双窟”一般处在同一水平,并列开凿,上下布置者则罕见。又78窟中已凿兜率天宫交脚弥勒及胁侍圆拱龛,无需再造同样大龛作“双窟”。又据早期崖面洞窟布局的分析,51窟等早于74、78窟,90、165窟等晚于74、78窟。指出此点,提请注意交脚弥勒菩萨脱离附属三世佛大龛而独立成龛,是晚一些时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