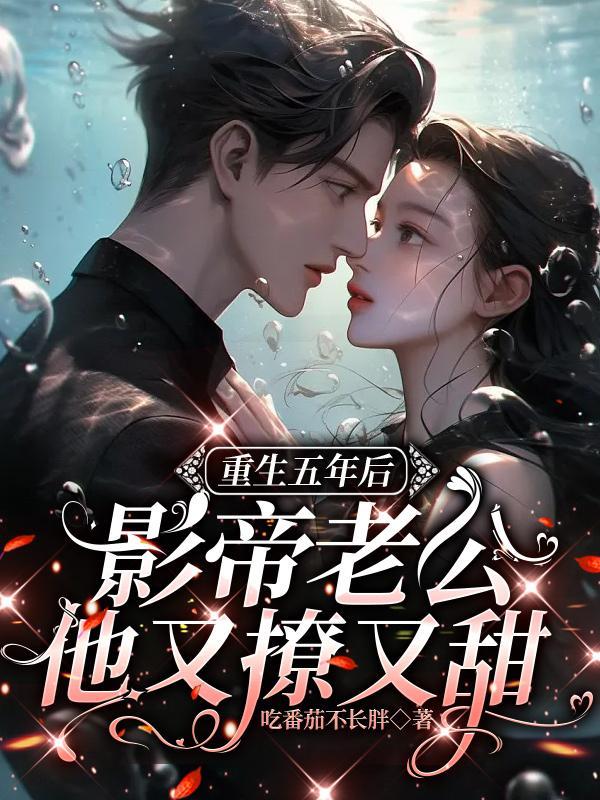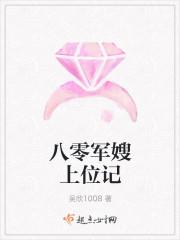456小说网>大明捉鬼记明朝那些魑魅魍魉 > 第135章 大捷众生相(第2页)
第135章 大捷众生相(第2页)
“因为不够封爵!”丁绍轼突然开口,“算计再精明也得注重脸面,若林威杀四千真虏就封爵,大明朝的武勋人人唾手可得,这是刨自己的根。”
他一开口,立刻吸引了三人的目光,丁绍轼就在顾秉谦身边,他突然拿过皇帝批示,“英国公还在禁宫吧?丁某去问个清楚,若让内阁下这道圣旨,林威必须对照李成梁功勋,休想凭借一次大捷让驸马都尉做勋贵,更别想勋贵外镇领兵。”
顾秉谦一把拦住他,一脸贱笑,“丁大人说的好,太子少保、少保、太保,三师三少三孤,林威必须一步步来,否则我们不用印,让后人头疼去,或者勋贵自己找一个敢用印的人来当阁臣。”
丁绍轼点点头,“这是当然!”
顾秉谦笑了,“这是朝政大事,内阁都去,否则我们都会被别人戳脊梁。”
黄立极和冯铨立刻附和,丁绍轼也不疑有他,四人一起出门,到乾清殿求见皇帝。
…………
注:
丁绍轼,史册边沿人物,但他不是小人物,估计很少有人关注过他,会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作者有必要浪费唾沫说说正史记录中让人迷惑的丁大人,以免后面看的迷糊。
他很特别、非常特别,浑身笼罩在历史迷雾中。
他的简历、立场、做事方式都非常‘有意思’,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底细的官员。
万历三十五年,丁绍轼四十三岁才中进士,当时浙党主政,一开始就备受青睐,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里不得不先提另一个人。
这时候的首辅,是史上辞职次数最多记录保持者,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谁?
是谁在16世纪就创造了这个记录?
答案是李廷机(估计很多人没听过)。
他遇到万历皇帝最懒的时期,首辅一年都见不到皇帝一次,朝廷完全变成了一个庙,中枢三千京官上上下下全是泥塑。
一般来说,三请三辞是‘做人’底线,李廷机五年时间内,上辞呈123份,最后也没辞掉。
估计他觉得这个数字不能再涨了,就此打住。
搞笑的事来了,竟然自己给自己下了一道公文,内阁首辅辞掉内阁首辅…拍拍屁股回家了。
朱明立国之初,朱元璋给官员定的俸禄太低,官员责任大,造成一个特殊现象,好多人撂挑子‘挂印而去’,人一多老朱大怒,但凡有人敢挂印‘不告而辞’,无论品阶高低,一律削籍下狱抄家,老子让你装逼。
从此朱明二百年,再没有官员敢未获准的情况下挂印。
李廷机犯了大忌,啪啪打脸皇帝,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但是…万历‘忘’了,皇帝忘了堂堂首辅,天下都不可置信,但皇帝就是忘了…
滑天下之大稽。
(这期间内阁只有两人,李廷机和叶向高,后者莫名其妙就成了独相,也是他第一次任首辅)
李廷机死了,皇帝才‘想起来’他是首辅,以最快的速度赐少保、谥号文节,嗯,还是美谥,让那些辛辛苦苦的臣子喷血。
李廷机任首辅五年时间内,不仅频繁请辞,还频繁给自己准病假,一准就是好几个月。
上梁不正下梁歪,丁绍轼就是‘追随者’。
丁绍轼中进士后,向朝廷求了个恩情,回乡接母亲到京城生活,嗯,先翘班一年(这里还有个常识,明朝禁止家属跟随官员上任,特殊情况必须得到礼部尚书、首辅或皇帝同意才可以,这是古代保持吏治清明的两千年习惯,避免官员亲属在地方弄权为祸)。
不到一年,丁母病故,守丧三载,服丧期满任原职,适逢湖广宗室华阳王册封,别人嫌路远不想去,他主动请缨去宣旨。
丁绍轼的骚操作又来了,到湖广宣旨后,扭头跑回家去了,一跑就是两年(娘的,在职却在家领俸禄,真让人羡慕)。
两年后,不知道那个‘不长眼’的想起了他,诏命回京领取两年供俸,他又‘病’了,‘神志虚弱’,又借口把家人接到京郊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