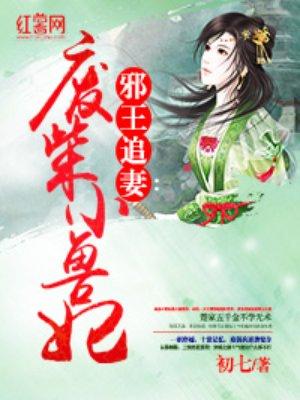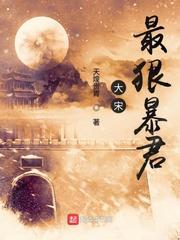456小说网>黄金家族从西域开始崛起的 > 第二百九十八章 众汗之汗(第1页)
第二百九十八章 众汗之汗(第1页)
戈壁阿尔泰山,乃是阿尔泰山东南方向的余脉,被此时的大漠汉人称作“南金山”。
比起真正的金山,这里少了几分高大险峻,多是些低矮的丘陵,丘陵间铺展着大片草原和戈壁,可容纳大军通行。
此时,南金山脚下的察罕泊周边,草原上却是扎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
每隔一段距离,便会插着一支纯赤色,或者黄底白边的日月战旗。
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翻滚的彩浪。
而每一面战旗,代表的便是一支百户。
在此休整的,正是来自西州的第二镇一万大军,和来自甘肃的第四镇六千骑兵。
合计一万六千人。
这支队伍清一色全是骑兵,每名士兵至少备着三匹马,多的甚至有四五匹。
马背上驮满了粮食、铠甲、武器等物资,足够这支大军半年之用。
而如此充沛的粮草,自然离不开张兴华和顾自忠对甘肃、西州两地的经营。
就像是西州巡抚顾自忠。
此人一到任,就雷厉风行地细化户籍、田亩管理,一门心思扑在农牧业上,天天催着百姓多开荒、多种田。
原本的高昌国就是北疆的粮仓,境内遍布着肥沃的粮田。
顾自忠把这些粮田重新梳理登记,租给汉人和回鹘百姓耕种,又组织人手开垦荒地。
如今西州的田亩总数加起来已有一百三十多万亩,比从前翻了不少。
更难得的是,西州的粮食大多能一年两熟。
秋日里种下小麦,来年夏天收割;紧接着种上栗米,秋天再收一茬,循环往复。
同时,还会根据需求和土壤情况,穿插种植高粱、大豆、棉花等作物,田地里一年到头都不闲着。
就说去年一年,西州境内便产出了两百多万石粮食,光收缴的租税就有九十万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九十万石粮食或许不算太多,但对于一个州府,这数字,历朝历代都难以企及。
要知道,过去大部分粮食都被中间的豪强地主、士大夫阶层盘剥走了,国家和百姓只能啃点他们剩下的残羹冷炙。
可北疆硬是砍掉了中间商环节,让官府和百姓直接对接。
官府按定好的租税收粮,不搞苛捐杂税。
百姓种多少得多少,缴完租税后剩下的全归自己。
如今西州仓库里的粮食堆得快溢出来,仓房都不够用了。
百姓家里的余粮也足够吃好几年,遇上灾年也不怕饿肚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湖畔的篝火旁,士兵们正用铁锅煮着栗米粥,香味飘出老远。
一个西州来的士兵捧着粥碗笑道:“咱西州的粮食就是瓷实,煮出来的粥都比别处稠!”
旁边的一名回鹘士兵,说着磕磕绊绊的汉语道:“那是顾大人会理事,搁以前高昌国,种再多粮也落不到自个儿嘴里。”
三娃子闻言,则是好奇的向其询问以前高昌的惨状。
原本以为自己很惨了,给田主当佃农,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
没想到这些回鹘人更惨,完全就是贵族的奴隶,别说吃饱饭了,甚至有可能因为主人的一个不高兴,直接将其打死。
北疆军来了之后,打倒了他的主人,给他们这些奴隶分了地,所以这个回鹘人在当兵的时候,比很多汉人都要积极呢。
而三娃子,原本便是河西的一名汉人少年。
当初北疆军攻占河西时,他被俘虏到了高昌,成了北疆的一名田户。
租了二十亩地,还娶了个回鹘媳妇,眼看着好日子正要开始,将军府却下达了征调一万大军北上的命令。
在兵役方面,北疆对平民也是有要求的,每户必须出壮丁轮流服兵役。
没有战事的时候,只需要隔三天时间,抽出半天来组织训练,算是民兵。
发生战事则是直接转化成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