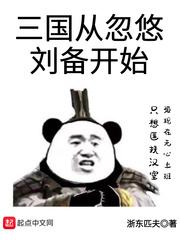456小说网>风过野梢 > 第五十七章 些许深沉(第3页)
第五十七章 些许深沉(第3页)
虽是五岁上就在家学里读书,但看那《说文》里还是有许多字不认识。
认字可不是自己能琢磨的,你不认识它,看千遍万遍,还是不认识,只能看个脸熟,再见了面,还是不知道咋称呼。
上了四年多家学,那是有专门老先生教的,还有那没有给过自己好脸色的爹,都拿一块尺长的板子。先生教,爹也时常考问,学得不认真,写不上字答不出问题时,都是要挨板子的。
现在想来,那学没白上,板子也没白挨,真要换个库要记帐了,学的那些字也能应付。
只是现在,没人教了。
想问师父,他也说过识不得的问他。只方才他的脸板得正经,这会也不知是不是睡了,宋双不想打扰了他。
偷眼看时,师父悄无声息地斜靠被子躺着,一动不动,眼却是睁着的。
那眼也是一动不动,只盯着房顶,只不知那房顶子又在不在他眼里。
平日里那总正经不起来的脸上,那总嘻嘻哈哈的脸上,忽然象是落满了孤独落寂。
还有,些许的深沉。
宋双轻轻地翻书,“碳儿”也舔净了毛,趴宋双脚边睡着了。
师父躺到晚饭时才起身,懒洋洋地去打饭。
这回端来的饭和昨日宋双打回来的一样实成,看样有昨日的剩饭中午吃得撑了,路上没偷吃。
也是中午吃得太撑,晚上这盆连饭带菜抄给了宋双大半。
“你小子闲得慌了,点个灯库里耍刀枪去,灯光暗,看书看得眼花呢。”袁老孬啐出舌尖上一粒糜子壳,“别给憋出病来,我象你这么大时,也是闲不住。”
一会儿让我一页页认字,一会儿又不让看了,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正合宋双心意,嘴上答应着,人已朝库房去了。
那库里的刀枪虽都是些钝头卷刃的破烂货,但又不是上战场,拿来练习还是很好的,宋双早就盯着那些兵器了。
门开着,叫漏些月光过来。
宋双拿起一把刀,忽然想起李黑的话,“最好是一砍一大片的大刀才过瘾”。
那刀只是普通的腰刀,长约一米,手里掂着也不过二三斤重。
宋双小时在家里虽习过武,但练的是拳脚。后来出了家门,也常与人厮打,砖头瓦块树棍子倒也随手拿来使唤过。真正的兵器,却是没用过的。
菜刀倒是用过一次,是拿去对付吴撇子的,虽能杀人,但好象也算不得兵器。
那东西,在伙房里是厨具,杀了人便是凶器。还没听说战场上用菜刀的,自然算不得兵器。
宋双没有用过兵器,那腰刀拿在手里,一时不知怎么个练法。
去,要什么练法,哪那么多事。只当对面来个人,拿刀拿剑拿棍或是拿斧头,或扎或砍或劈或砸地要杀我,我得挡住护住自己,也得去砍去刺他。
无非就是防和守,至于招势,这刀尖能扎刀刃能砍逮着空子用上就是。
对,就这么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