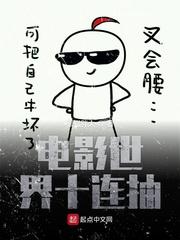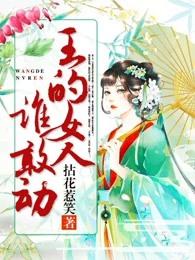456小说网>落魄秀才不如狗 > 第27章 初露锋芒(第1页)
第27章 初露锋芒(第1页)
前些年,不是有个姓周的户部大官儿,想伸手查查这漕运上的烂账吗?结果呢?还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了?听说啊,那漕运总督衙门里头,从上到下,早就穿一条裤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陈望亭心里“咯噔”
一下,面上却装作恍然大悟的模样,连连拱手:“原来如此,多谢老哥指点迷津,小子明白了。”
从杂货铺出来,陈望亭心里更有数了。
基层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藏着的只言片语,往往最能印证那些账面上的猫腻。
他又去了几处与漕运相关的牙行、车马店,或买或问,旁敲侧击,装作打听行情的模样,零零碎碎又收集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当晚,陈望亭回到自家书房,反锁了房门,点亮桌上的油灯。
他铺开纸张,开始奋笔疾书。
这次,他写的可不是那些辞藻华丽、引经据典的策论,也不是给皇帝老儿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
而是一份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每一个字都透着冰冷寒气,直指要害的分析报告。
他没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推演,而是简单粗暴地将新旧账目中的疑点,分门别类一一罗列,再把他白天打听到的那些“小道消息”
和市井传闻作为旁证,附在后面。
逻辑清晰,证据链完整,让人一看便知其中深浅。
譬如,某段河道清淤,账面上清清楚楚写着用工五百人,耗时两个月。
但他从当年参与过工程的老民夫口中打探到,那段时间真正下河干活的民夫,撑死了不过两百人,而且稀稀拉拉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草草收场。
那多出来的三百人的工钱和多算的一个月工期,银子进了谁的腰包?
又譬如,某批漕粮从江南转运至京城,账面上报损三成。
但他从相熟的船老大私下闲聊时得知,那一趟风平浪静,粮食保管得也妥当,实际上的损耗,连半成都不到。
那凭空消失的两成多粮食,又喂饱了哪些人的胃口?
一条条,一款款,证据未必都凿凿可据,但蛛丝马迹串联起来,已然勾勒出一个盘根错节、触目惊心的贪腐网络,深深扎根于漕运系统的每一寸肌理。
写完详尽的分析,他又另取一页,笔锋一转,写下“应对之策”
四个大字。
他没扯那些“严惩不贷”
“彻查到底”
的官样文章,而是直接上了几条简单粗暴,却可能立竿见影的狠招。
其一,账目交叉审计。
户部和漕运衙门自查自纠那是糊弄鬼,必须引入第三方,比如都察院那帮喷子,甚至可以从地方上临时抽调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愣头青官员,搞突击检查。
部分账目直接公开,让老百姓也瞅瞅,这钱都花哪儿去了。
其二,设立“漕粮监督官”
。
从京中那些油盐不进的御史,或者干脆从军队里挑些杀才,六亲不认的那种,直接空降到漕运的各个关键码头、粮仓,从装卸、转运到仓储,全程给老子盯死了!
权力给足,只对皇帝老儿一个人负责!
其三,改革耗损核定。
不能再由漕运那帮孙子自己报多少就是多少。
得根据实际的天气、路程远近、物资种类,搞个相对统一但又有点浮动空间的耗损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