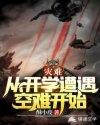456小说网>林昭简历 > 第112章 生啥她也能做主(第1页)
第112章 生啥她也能做主(第1页)
阳历新年一过,就是八零年了。
改革开放的风已经吹到了北方,村里的土地也都开始承包,各地掀起了投商引资经济先行的热潮。
也允许干个体,原本的公私合营,可以个人承包。
秦生生第一时间就把鸡架厂和饺子馆的公方股份买回来,成为真正的个体经营。
原来公方的经理老牛和会计舒春芬,就是从街道选上来的,不是正式的编制,公私合营结束了,他们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秦生生也没有放他们走,老牛是老牌街溜子,继续留在饺子馆,也不说给什么职务,还拿原来一样的工资,见官大三级,啥都能管管,当个吉祥物一样的养着。
舒春芬的会计水平不错,这几年处下来,也算是能信得过。刚好新开的包装厂得派个自已人过去,就把她派到了包装厂,副厂长是爷爷的警卫员段永胜帮着联系的,一个因伤退伍的老兵,刚刚退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人很精明,又可靠。过去不用参与管理,就看着王得福他们,起个监督作用就可以。
个体经营的繁荣,带动的就是家庭收入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各行各业的兴盛。
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筑业。有钱了,大部分人最迫切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十几口子住三四十平的筒子楼的情况,不是迫不得已,谁乐意那么将就啊。
有钱建房了,原本的荒地,闲置土地都成了香饽饽,就比如张向阳和白英杰兄弟当初买的老印刷厂那一片地,周围陆陆续续都被买完了,城郊和军区这一片,也算是彻底的连接上,再没空地了。
就这,陆续的都有人买后排的地,不临街除了不能建门市房,纯住的话,并不影响什么。
哪怕没钱买地建房的,有了余钱,出去租个单间住,也是有独立空间了,比挤着强。有这个需求,有私房的人家,建门房出租就成了好买卖。
有需求就有供给,建房的人多,需要的建筑工人就多。红旗大队的李常胜常跑省城,发现了商机,秋收过后,就组织了大队的青壮,拉起来一支建筑队,进城找活儿干。冬天不能打地基建房子,那不是还有屋里的零活儿能干嘛。
反正一直到过年,都不闲着,一个月零散着挣上百八十的是能。
手里有钱,又快过年,肯定要消费啊。
吃点儿好的,不过分吧。
饺子馆的生意,忙得都快飞起来。
相应的,钱挣得也快。
这日子,人人都说,蒸蒸日上了。
非要老百姓说有啥不那么满意的,就是计划生育。
“只能生一个娃了,还怪孤单的……”
姥姥姥爷家里七个孩子,六个大的都是一儿一女,只小姨生了一个独苗苗。
不能再生了,老两口就觉得挺遗憾。
沈士英怕秦生生多想,赶紧把话往回拉,“工作忙,没那么些精力照看,有一个就行了。小沈家里就一个,不也挺好的。”
这一说,姥姥一想,“哎哟,说起来,沈家这都三代单传了吧?”
是呢,“奶奶就是独生女,没什么直近的亲人了,又只生了我公公这一个,公婆又生了沈白一个,沈家不算,从白家这边儿算,刚好三代单传。”
“那他们家不会有啥别的想法儿吧?”
啥想法?秦生生一时里没听明白姥姥啥意思。
“就是想要个男孙传宗接代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