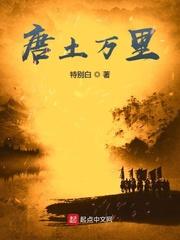456小说网>故人与往事 > 第四十七章 老娘卖猪(第1页)
第四十七章 老娘卖猪(第1页)
第四十七章老娘卖猪
人和村在山东的边上,紧靠着江苏,村南就是苏鲁边河,属于鸡鸣两省的那种老村落。记忆中,边河的那边是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隔河和那边的孩子们对骂、扔坷垃头子,那是常有的事情,尽管什么都不因为,都属于吃饱了撑的,野惯了无处发泄,没事找事。
而出了村,不往南走,往东走的话,走上几里路,再跨过苏鲁边河的边庄桥,就到了江苏的龙巩镇地界,再往东南走几里地就到了龙巩集。
龙巩集是苏鲁交界处的一个大集。平日里买菜、买点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就赶村北一里远的严集,而我姥姥家很久前贩卖大牲畜、我家卖小猪崽的时候就要到龙巩集去。
一九七几年时,响应伟大国家号召,公社推行“斤猪斤粮”政策,并采取五帮措施。得益于老爹在粮食部门工作,能够买到猪饲料,我家早就养猪,这一次更是紧跟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力养猪,猪最多时我家曾有两个猪圈,两头母猪。养猪能积肥,肥交到生产队给工分,养肥的猪交到公社的收猪站卖了钱是自己的,每斤猪大队里还给粮食、还算工分,一举多得。那时,每年底,小队的会计程二平算工分时,都会在那个满是化肥味的低矮的小队仓库兼办公室的墙上,张榜公布出来,对我等贫困户神气得很,我家每年都要拿出几十块钱交到队里。现在,我家终于扬眉吐气了,再也不用低人一等似的,再也不用交钱到队里换工分分粮食了。队里分粮食了,老爹老娘兴高采烈,满满的一车粮食往家拉,我则扶着车帮帮着往家推。家在村的最西北角、大队妇女主任康秀云,看着我家满车的粮食,恨得两眼冒火。我家进入到小康时代,成为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拨。轻轻地挥一挥手,作别程二平式的嘲笑,我家的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羡慕和嫉妒。当时的队里,即使家里有最好的劳力,全年没白没黑地干,你全家也多分不到一百元钱。
自那时起,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家养猪,而且养老母猪,最早养的是头黑毛的老母猪,通体黑色,就猪蹄子有点点白的。老母猪,个头奇大、膘肥体壮、毛色黢黑溜光、双眼叠皮的,属于母猪里的大美女。
我曾多次跨到它背上骑它,但无奈没揪手,我的腿太短又夹不住它硕大的肚子,它嗷嗷着不让我骑,跑来颠去的几下就把我甩下来了。
我家这个黑美人,不只样子俊,而且很能生,是一个很能生养的大美人,绝对的生育高手。每年它都能产两窝崽,一窝猪崽怎么也有七八个吧,两窝猪崽就是十好几个,一个猪崽卖三十块钱的话,一年下来在农村就是巨款了。那时,一个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人一个月也就是挣三四十块钱,我家的这个黑美人绝对是能生能干能挣钱啊!
每次,刚下崽没几天就有同村人来我家看小猪,相中了哪头后就给号下了,只等小猪能自己吃食了再抱回家去。
小猪长到一个多月时,不用吃奶能自己吃食了,我娘就告诉人家来抱,称好了有给现钱的,也有赊着的不定啥时候给钱的,乡里乡亲的又不会去讨要,都是啥时候宽裕了啥时候给。
每当人家来抓小猪时,就要把老母猪赶到一边去,不让它看到小猪被抓,不让它听到小猪叫。每次肥嘟嘟油光光的小猪被人抓走时,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就想着小猪在我家多快活啊,到了人家家里还不知道怎样呢,还不是要受罪。我老娘就经常说,唉,咱家的小猪到了别家也养不好,他们家的猪食哪有咱家的好,咱家的稻糠都是你爹弄过来的,攥着都出油,猪吃起来还不长得快。到了别的家,吃得糠没有油还粗,就长得慢了。
我家的小猪好卖得很,属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七十年代里,农村的条件还是差很多,靠吃粗糠吃青草猪是长不好的。因此,每次下了小猪只靠同村人抓是不够的,有时还有剩下的小猪,我家自己也养不过来,就要到集上去卖。
每次卖小猪时,全家人会起得很早,先给小猪喂饱了,再把老母猪赶到一边去,省得我们抓小猪时小猪叫唤,老母猪舐犊情深地闹腾。再说了,说来也算是母子分别,就叫它们悄悄别过吧,不然,叫唤得怪让人伤心的。
捉来的小猪会被放在筐子里,就是那种大肚子、细脖子的筐子,紫荆条子编的那种。把筐架到地排车上,用绳子拴好,就等上路了。
大多时候,赶龙巩集的活都是老娘和我一起去的。要去赶集了,而且干的是家里的大事,我觉得无比神气,在弟弟妹妹面前挺胸腆肚的。
在弟弟妹妹的艳羡中,我和老娘出发了,老娘架着地排车,我拉着梢子。
我去干大事了,弟弟妹妹只有在家等着,等着我们回家捎好吃的吃头回来。
这个时候,天还很早,也有雾气蒙蒙的时候,我和老娘会急急忙忙地赶路,娘俩也会不时地擦擦汗。
赶早集赶早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老早地到集上去,赶个好行市,遇个好买主,兴奋盎然地赶路。我们老家形容谁慌慌张张的忙活,就是这样说的:看你慌慌哩,给赶严集样。
秋天的清晨,天色蒙蒙亮,太阳的踪迹尚在地平线之下,一条狭窄的马路蜿蜒伸展,路两旁是随风轻摆的芦苇丛,仿佛低语着清晨的秘密。空气中弥漫着新鲜而又带着凉意的泥土香,沁入心脾。
马路上,露水沾湿了尘土,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迹。偶尔,老式的自行车铃声清脆响起,打破了这份宁静,却又迅速被四周的寂静吞噬。芦苇的穗子在微风中轻轻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似乎在诉说着秋日的往事。
远处,几栋简朴的农舍隐约可见,屋顶上飘荡着淡淡的炊烟,那是村民们开始新的一天的信号。鸡鸣声与犬吠声此起彼伏,为这个清晨增添了几分活力。公鸡的啼声高亢有力,划破黎明前的黑暗,而犬吠则像是对即将到来的日出的一种期待。
天色尚早,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去龙巩集我小姑家走亲戚,也是走这一条路。以后的许多年,这条窄窄的马路,见证了太多这样的清晨,它沉默寡言,却承载了无数人的故事和岁月的变迁。
太阳逐渐露出笑脸,光芒穿透薄雾,洒在这片土地上,金色的光辉与芦苇的绿意相映成辉,一幅静谧而又充满生机的画卷徐徐展开。
在去往龙巩集的马路北边,孤零零地高高立着一个墓碑,据说是一个拉练的解放军战士,像欧阳海那样为了抢救集体财产牺牲了。
第四十七章老娘卖猪
这里的马路更窄,马路两边生长着一丛丛高大的芦苇,每到此处,芦苇被风一吹,沙沙响着,起伏摇荡。
此时的我都会害怕,而老娘就会给我说,让我咋呼咋呼给自己壮壮胆,就不害怕了。
多年以后,我再经过此处时,墓碑已经不见了。
龙巩集是苏鲁边界一个很大的集市,源于它经济起飞比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