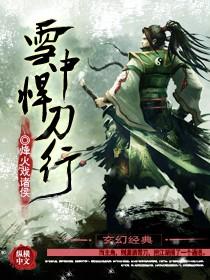456小说网>和往事和解 > 第四十三章 老院老屋(第1页)
第四十三章 老院老屋(第1页)
第四十三章老院老屋
人和村是一溜十八团里西数第一团,村中的人大多是清朝中叶从郓城、巨野逃难到此定居的,因此,人和村的风土民俗和鱼邑县内其它地方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
我家就在人和村,村北门进去左转,第二家再右转,往南再走第二家便是。
人和村是个大村,有近三千人,一个村落分为人北、人南两个村治辖区,人北村又迁移人口到了村西北方向约四里远处,新建了一个人北新村。
人北村的人,才是人和村最原始的原居民。人北村全村被护村坑环绕,只在村东、村西、村北留有寨门,而人南村的人则全在护村坑外的村南。护村坑宽而且深,是从外地迁徙而来这里的团里人,为了卫家护院倾力而挖。团里人,有血性、性情刚烈、直率、讲义气、能吃苦,经过一百多年的械斗,死伤无数的人命,而得以在这里生存、繁衍,逐步站稳脚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人和村人的口音、性格、风俗习性、生活习惯,无不传承着团里人永远无法改变的印记。
人北村在人民公社时代有八个小队,我家就是四小队的。四小队有一百多口人,分别有商姓、袁姓、王姓、程姓、魏姓、翟姓等。人和村就是人们所说的杂姓村,这和人们的迁移史有关,但许多的杂姓人聚在一起,团结一心、抵抗外侮、争水夺地、共同生活,也着实不易。
我的家是在一个高台上,走进胡同逐步向上,步步抬脚就到了我家门前。站在我家的门前,往东望去,明显高出许多,而门前的路东下又是一个和护村坑相通的大水坑。
这个大水坑,最大时有十余亩,从南到北沿中间划线,分属于三小队和四小队。一到夏天,水坑里便是满池的荷花,是那种大朵的白灿灿的白莲花、粉艳艳的红莲花,从小荷才露时我们就打荷叶玩,及至莲蓬长成,吃起来满嘴留香,脆生生甜丝丝。一旦我要下水够莲蓬了,就会吃个痛快,我家的大粪坑旁就堆满了我们吃过的莲蓬皮。到了冬天,这里又是天然的溜冰场,我们在这里溜冰、打拉拉牛。
大多时候,站在我家门前,凭高望去,荷叶田田、荷花盛开,微风吹来,荷叶起伏偶有白底次第翻过,荷花颤动偶有花瓣簌簌飘落,更有荷叶荷花的香甜气息飘来,沁人心脾、神清气爽,莫不让人感到如临仙境,心旷神怡。
我家的祖屋,也就是我奶奶住的地方,在我家的西南方向二百米处,祖屋也是地势很高,门前有四小队的水井一口,全队的人都吃这一口井里的水,水井西挨着又有水坑一口,也是通往西护村坑的。
无论是祖屋还是我家的“新屋”,门前都有水,自我爹一代,商家我们这一支也逐渐兴旺起来,绝对有风水的因素。曾经有风水先生经过我家门前时,就不住口地赞叹过。这点,我是信的。
一九六二年,二十二岁的我娘嫁到了老商家,而自从嫁过来就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
又过了两年,我老爹当兵复员回家,带回来了一百多元的复员安家费。村里的老徐家扒屋,就买了人家几根梁椽。大队里看复员军人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公家的梁椽也算便宜照顾给了几根。老爹去龙巩集又买来高粱秸编成箔,于是老爹老娘开始建房。
那时,我广中舅已经从曹县回来,在大队当着干部,就是他照顾的我家买的梁椽,这个是不能忘记的。
好在老商家还有一处老宅子,于是,老爹老娘原地起土,垒起了第一茬土墙。然后,我娘和我爹一车一车地拉土,垒起了第二层、第三层,终于盖起了三间房子,我爹娘住在西面的一间里,我就在此出生。
一九六七年的腊月里,我妹妹出生,家里不是我一个孩子了,房子太小就住得艰囧了。
近门的二爷爷老两口无儿无女,远居大连多年,他在人和村有老屋一口,商相同的老娘借住在那里。商相同的老娘就邀我老娘过去住,于是我家准备住过去,好在很快,商相同的老娘就去了东北找她儿子去了。
记得那一年,约在一九六九年冬天,我们搬家了。刚满三岁的我搬不动东西,但也来帮忙,搬着一个小缸似的东西,从袁存芝家过,我就在他家院子里门前停下来,扶着小缸。那一刻是我最早的记忆,在祖屋的日子我一点点记忆也没有了,以后所有的能记起的都是搬家后的事。
我们借住的屋子是一座老屋,共有三间,孤零零的,偌大的院子连棵树都没有,房子高大空旷,墙面黢黑,屋顶的秫秸箔也是黑黑的。
这样,住了有些日子,大连的二爷爷来信了,说是不借给我们住了,要卖给我们。既然是借住,自己家没房子,那就买吧,也就回话过去。很快,大连给话了,要五百元钱。讲价钱时,还有村里有名望的袁广良、程衍东也是做了中间人的。我的个天,这在当时可是巨款啊。此时,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家人辛辛苦苦年底算账落下一百元算是很好很好的,为了买工分我家每年要贴几十元,而在公家部门上班的老爹,一个月工资也还不到三十元。五百元钱的话,相当于老爹两年的工资。可怜的爹娘,在几十年前,在未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的年代就沦为了房奴。当时的平常百姓家没有存款,更不兴个人消费贷款。为了筹措房款,当年的爹娘愁白了头、操碎了心。好在二爷爷知道农村人的苦,没让我们一次付清,手头宽裕就多付点,手头拮据就少付点。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有了自己的窝了,昔日的一家人就和今天贷款买房的房奴一样,尽管身负巨款,总算有了栖身之处,有了自己真正意义的家,幸福感、归属感倍增。
但不知是何日,老爹说,大连的二爷爷又来信了,说要再给他加点房钱。在叨叨了多次以后,在叹息了多次以后,家里也实在一点钱没有了,我爹娘又咬牙,欲拆东墙补西墙,可哪有东墙可以拆?只有借了东家磨西家的,给他寄过去了些全国粮票。那个年月,买粮食只拿钱是买不到的,还要拿粮票,因此,粮票就是钱。这就是我的爹娘,明明讲好了的价付过了的钱,总觉得人家万一有难处呢什么的,咬牙自己承受。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家,在我几岁的时候,隐约记得爹娘商量钱的事,隐约感受到了父母所承受的苦难!
第四十三章老院老屋
若干年后,漂泊大连多年的二爷爷二奶奶落叶归根了,回到了人和村,就住在了我奶奶的老屋里,一直到老两口去世。曾经的我们借住他家,如今的他借住我家,这是不是轮回。而他们在人和村的那些年,和我的老爹老娘关系一直都很好,尽管在商家的近支里我们和他不是最近,他死时摔瓦罐也轮不到我家。
那一日,我和老娘到西南小洼子地里去干活,我还很小,走走就累了,干了农活的老娘也是很累,于是娘俩个就坐在路边,老娘从兜里拿出来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娘俩个垫巴垫巴。我们吃的是花老虎卷子,就是一层白面一层黑面卷起来的,老娘就吃黑面的,把白面的一层层掰下来给我吃。这是我关于吃的最早的记忆,我吃白面的,老娘吃黑面的。那个年月,吃点全麦面就是富人家。
最早的时候,家里连个厨房都没有,做饭都是在那三间大屋里,依稀记得烧锅的地方、织布机摆放的地方。
老屋的院子方方正正,很大,老屋就在院子的东北角上。院子南边、西边有人家,我家没有院墙,就是孤零零的一座大屋。
因为没有院墙,家住我家西北面的人,到村南、村东去的,来来往往就从我家过,来福、二孩、德州、花妮上学时都是从我家过。
院子的东南角有一个猪圈,有一头小猪养着。
院子南边,正对着堂屋大门的,有一个粪坑,就是农村倒垃圾、锅灰的地方,以备攒点粪肥交到生产队去算点工分。那时的人们,吃得稀,没有多少油水,稻草麦秸的烧成灰也没有多少,偌大的粪坑也并不臭,没有多少东西。只是每次队里来拉肥了,我老娘一次次多培几锨黄土充数,硬生生地把粪坑挖大了。及至某一天,粪坑里积满了水,小海州一不小心滑了下去,粪水及腰深,自己哭着爬也爬不出来。我老娘一把叉子把他叉上来,再把他全身扒个溜光,把他的衣服全部踩在沙土里,翻来覆去地踩,踩踩抖抖再踩踩,烧把火一烤,“啪啪”狠劲地拍打拍打,给他穿在身上,嘿,身上的衣服像洗了一遍似的,比以前干净多了,小海州嘻嘻地笑着又疯去了。
院子很高,每次我从外面玩够了,回到家里,看到家里没人,我就会站在大门前的高台上高喊:娘来,娘来。一边喊一边玩,也不急的样子,反正知道走不远。
院子很大,刚刚搬家过来时,老娘买下了榆树苗,我扶着树苗,老娘铲土,就种下了许多榆树。老娘说,等榆树长大了我就长大了。我小时,老娘就老盼着我长大,说等我长大了就中用了。
在榆树很小的时候,院子很空旷,于是老娘就在院子里种点菜、种点葱。记得最清楚的是,院子西南角种了很多北瓜,一颗颗的拖拉很长。长了很多北瓜花,老娘就摘来,蘸点面油煎了吃。那时,家里的油都很金贵,虽然油很少也很好吃。记得,我和家北的大彬在北瓜秧里玩耍,他总也抓不到我,他就咧咧嘴笑笑。
北瓜熟了,吃得最多的是馏北瓜,就是切得一块一块的,放在篦子上蒸。待到蒸熟了,老娘就一人一碗地分给我和妹妹吃。那时的北瓜,掰开来黄灿灿的,很面很甜,软糯糯的,面得噎人,甜得齁人。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吃头。以后,我再也没吃到过这样好吃的北瓜或南瓜。
一九七零年八月,刚刚过中秋节,我的二弟出生在老屋里,此时,大概是我们家最穷的时候,倍尝着生活的艰辛;一九七四年四月,麦子扬花时,日子勉强有点好转,但也还是艰难度日,我的三弟出生在老屋里。我家子妹四个也算都是在苦难里过来的孩子。
三弟出生的时候,他是那波孩子里几乎是最小的,那时家家户户都是一大群孩子,整个村西北角就是孩子们的乐土,没个肃静的时候,不是这家叫就是那家哭的,热闹极了。
夏天的傍晚,喝汤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要把饭桌搬到堂屋的门前院子里,老娘就把汤舀到盆里面端过来,放在饭桌上,等汤冷凉点再喝。子妹几个围坐在一起吱吱歪歪、热热闹闹的,虽是粗粮淡饭,但掩不住孩童时代的欢乐,掩不住一群儿女齐聚父母膝下的幸福。
夏天的院子里,榆树下,经常有爬叉爬出来,有时候还能爬到饭桌腿上,给我们带来欢乐。
喝过汤了,家北的大彬家、大庆家、建民家,几乎家家户户拉来苇席来到门前,我也会拉来苇席就铺在门前的二坡沿上,大人们忙完也会过来。几家的孩子,这时候是最疯的时候,跑着、打闹着。疯累了的孩子们会躺在草席上,用粗布床单整个地盖着自己,只露着头在外面,防备被蚊子咬,大人呼扇着竹扇子,一边给孩子扇蚊子,一边张家长李家短地拉着呱。自然,我家的条件还是要好一些,老爹买了驱蚊油,老娘就给我们抹在腿上、胳膊上,就少挨了些蚊子咬。其实,那个时候的蚊子还是多,咬上几口也感觉不到什么,后来离开农村,蚊子咬上一口,就觉得疼痛,就是红肿一片。
天上繁星闪烁,水坑里一片蛙鸣,很快有孩子睡着了,大人们又呼儿唤女地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