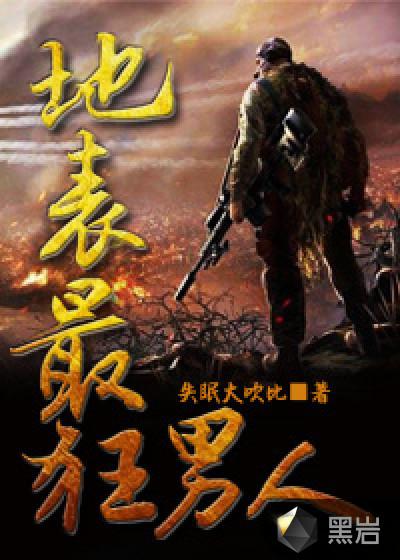456小说网>重生七零玄学老祖 > 第14章 离婚可没那么简单(第1页)
第14章 离婚可没那么简单(第1页)
杨舒芬牵起丫头往自家走,从屋里取出一碗草药膏之后,就在她脸上厚厚涂抹。
“这药抹上之后,等半个小时干透了再揭掉,连用半个月,脸就能光光滑滑。”
黑乎乎又发青的草药膏,抹在脸上先是凉丝丝的,随后就渐渐变得腻黏湿热。
奇怪的感觉还来不及细细感受,不耐烦的林栋梁就皱着眉走进来,将自家丫头给拽走了。
“你弟还没吃早饭呢,磨磨蹭蹭。”
“就算脸上没麻子,这鼻子眼儿也生的不咋地,小小年纪的,臭美个啥劲儿。”
林栋梁急着叫自家大丫头赶紧到供销社带粮回去做饭给三个小的吃,对自家大丫头没有分毫的耐心。
更别提顾虑难听话会叫丫头自卑。
吴娟倒是对大丫有几丝心疼,但这个连生存都难的世道,压的人喘不过气,也没气力去做些什么。
林栋梁拎着林丫走远之后,杨舒芬抱起小孙,步履蹒跚的去山里忙活。
而家院内外的动静,谢建国都听和看了个清楚。
他早先还以为老娘叫他捣腾牛筋草,是弄来给他拿去换钱的,从公平的角度去想,老娘就该是这样盘算。
哪想老娘根本不是这意思,草药膏居然是弄给麻丫用的,不是给他拿去换钱的。
这叫谢建国心头气闷不已。
夜里少睡俩小时开私田,大早上的起来困的要死。
又添了这份堵还没算完,老娘前脚刚走,何花兰后脚就从屋后头小心翼翼的冒出头来。
看见何花兰,谢建国气的呀,都没劲儿气了。
她是被亲爹何国庆给撵回来的,昨夜就给她撵走了。
毕竟晚上留她的话还得一顿晚饭,早上又是一顿。
撵走能省两碗饭。
这年头,谁家的粮都是有数的。
“建国,真是闹误会了,赶巧了才碰上的,不是你瞧见的那样。”
何花兰一进院子就跪在了地上,满脸都是乞求不离婚。
谢建国太累了,累的都没力气搭理她。
一声不吭就扛着锄头去了责任田,找机会猫田里打个盹儿。
又困又累的,打盹儿要紧,真没劲儿再置气。
这会儿不找机会打盹,夜里开私田啥的就更别想,老娘那话就跟悬梁刺股似的戳着他,毕竟是可能要命的事儿,根本不敢松懈下来。
何花兰还以为谢建国原谅她了,心里也跟着松了口气。
杨舒芬采摘野菊花,一路采摘,一路来到北边的山头。
旱年叫南边的山头黑漆漆一片,北边倒还好点儿,一个个山包连成片,山包与山包之间的坳子沟,歪扭着蜿蜒成狭长一道,好赖能攒些水汽。
有野草的地界儿就会有吃草的野味儿出没。
杨舒芬用镐头在一边杂草丛里一顿挖,花了个把小时,挖出一道一米多深、三米多长、宽度不到二十公分的窄坑。
再用镰刀割几茬儿杂草浅浅铺在上头,将窄坑给掩藏起,专门逮兔子的陷坑便布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