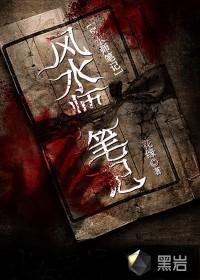456小说网>七零年代玄学大师家中有二 > 第7章 下地干活各怀心思(第1页)
第7章 下地干活各怀心思(第1页)
杨舒芬带着小孙在山里忙活大半天,来回三趟,采了三背篓的野菊回来。
瞧见小儿竟主动在灶房里忙活烧饭,杨舒芬高兴啊。
本想先调教好大儿子,再上心小儿子的事儿,哪想小儿子就是更聪明些,随手带一下就开窍三分了。
“妈,肉汤就要炖好了,您进屋歇着去。”
谢知远高兴不已,比起昨儿,精气神儿都神气了不少。
“诶。”
杨舒芬应了一声,扭头看向院子的另一侧。
谢建国正垂着脑袋单独生火烧稀饭,时不时就微微抬头瞄一眼灶房这边。
何花兰则正淘洗着玉米碴子。
好好的一个家,过的像两家人似的。
至于杨舒芬心里是怎么想的,很简单。
何花兰这个儿媳,问题很大。
仗着皮囊有几分姿色,结婚前在他们村儿就是风言风语。
若不是大儿子被她的姿色迷的鬼迷心窍,她没法只能默许了。
她这个当娘的当时要是反对,在他们看来便是恶毒的未来婆婆棒打鸳鸯,真以为自个儿是苦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大儿子肯定一辈子记恨自己这个当娘的。
她得让大儿子亲眼的一步一步瞧清何花兰的真面目,自个儿死心,然后主动跟何花兰离婚。
“别烧稀饭了,知远这不是闷了饭炖了肉,一家人起两个灶,叫外人瞧见还以为咱老谢家已经分家了呢。”
杨舒芬主动开腔招呼一声,何花兰和谢建国当即面露喜色。
有肉吃了。
何花兰还以为今儿又吃不上呢。
饭桌上,杨舒芬瞧着一锅肉汤,亲自拈勺分肉汤。
先给小儿子知远盛了一块肉、一勺汤,又同份量的给大儿子、大儿媳亲自盛了一碗,还有孙子兴兴。
谢知远心里有意见,但是算了,他不想吃饭时说难听话叫老娘心里添堵。
建国心里也有点虚,本来春节特供的粮票该交给娘的,然后娘会将粮票存到粮本里。
现在粮票在自个儿兜里揣着,他不愿意拿出来。
因为老丈人那边隔三差五就会过来串门儿,农村总讲究个人情世故,串门儿说白了就是来串伴手礼的。
作为女婿,你总不能叫老丈人空着手回去,那太难看。
而且何花兰也隔三差五的要这要那拎着带回娘家。
今儿是弟弟的学校要交课本费了,明儿是丈母娘腰疼腿疼得花钱买药。
谢建国当初为了能娶何花兰过门,跟老丈人家打了不少包票,结婚五年来,一直在打肿脸充胖子,就怕遭戳脊梁骨。
一顿饭功夫,各有各的心思,而杨舒芬平静的就像家里无事发生。
实则心里在惦记着不少事儿,撇开俩儿子的,就是大闺女谢桂花,自己亲生的孩子不可能不惦记。
“妈,您明儿多烧些桑菊茶吧,”
晚上正要歇了,谢知远笑嘻嘻的走进屋来,眉飞色舞的说着今儿的情况:
“妈煮的药茶有效果呢,化工厂的老乡可帮衬,一眨眼功夫就给分买完了。”
“明儿就算一百杯,兴许都能给卖完。”
一百杯就是五块钱了,谢知远越想越激动。
“不行,一天带三十杯过去就成了。”